長篇小說,文學的項上明珠。全面復雜、人物豐富、情節跌宕、結構精巧、哲思深入……一部好的長篇小說往往會被譽為“時代的百科全書”。
不過,薦讀一部長篇小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講求效率的今天,且不論創作的好壞,普通讀者已然少有耐心愿意去品讀一本“大部頭”了。你要是再談起什么家族興衰、時代縮影,怕是會起反作用。
這對讀者與作者,乃至文學發展來說,都無疑是一種遺憾。
01
近日,葉兆言全新長篇作品《璩家花園》由譯林出版社出版。這是作者現有十四部長篇小說中,體量最大、故事時間跨度最長的作品。以南京城南一座老宅院為背景,故事從20世紀50年代講到了幾年前,書寫了兩個家庭,三代人悲欣交集的人生。書的推廣語稱其為“時代的記憶”,是“平民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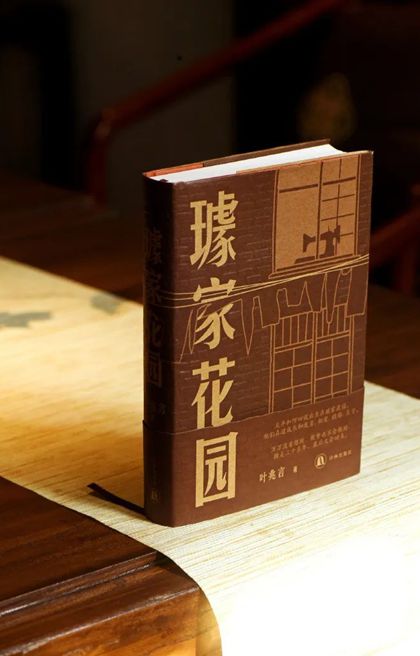
譯林出版社 供圖
可千萬不要被宏大的定語所嚇退。讀過你就會發現它的輕盈、平實、真誠。
刨去技巧、立意之類專業角度不談,從某種程度上,“好讀”是《璩家花園》最顯而易見的特色。別看它厚,如果你愿意,幾乎不用歇一口氣,花個一天兩天能順暢地讀完。用豆瓣上一位讀者的話說,“把故事從頭讀到尾,感覺像是跟作者聊天一樣,聽他絮絮叨叨地說著,我在沒頭沒腦地問著”。
正是這種痛快十分的體驗,讓人仿佛回到了在被窩中挑燈夜讀的學生時代。那激情澎湃、欲語還休的心境,是文學才能掀起的波瀾,實在令人懷念又感慨。
對于文學作品來說,“好讀”的另一個近義詞是“通俗”。“通俗”是不是一個好的評價?各有各的看法。葉兆言倒是非常坦率,曾撰文《小說的通俗》直抒胸臆,說“小說本來不是什么大學問,小說本來就是通俗的東西”。
如果說,“被看見”是文學實現其價值的前提,那么《璩家花園》勝就勝在了這份“俗”。
小說的角色都是普通而平凡的“俗人”,如每一個你我,或者身邊親友。
璩天井,一個像“阿甘”一樣的傻小子,看起來似乎除卻成功和喜歡的姑娘共度一生之外,其余一事無成,沒有享受任何主角光環,甚至還有些糊里糊涂——糊涂到在高考恢復后考上了好大學又沒去報到,又糊涂到連那位姑娘給他“戴綠帽”都毫無察覺。
那些配角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沒什么身份顯赫的貴人、天賦異稟的奇人、或是剛正不阿的偉人。他們不好不壞,游走在人性的灰色地帶;他們不算成功也沒有跌入塵埃,普通人大多如此狀態。相比遙不可及的“大人物”,他們的面臨的抉擇、困境、心態才能與大多數人達成共鳴。
小說的故事聽起來都也都是些“俗事”,盡是時代滾滾車輪碾出的家長里短。
就像莫言和高密,汪曾祺和高郵,張愛玲和上海,葉兆言是和南京深度綁定的作家。他書寫了南京城四十余載。不過,除了后半段出現的“鹽水鴨”,《璩家花園》的南京味并不太重。實際上“鹽水鴨”換成“姜母鴨“北京烤鴨”也未嘗不可。就連故事發生地“璩家花園”究竟在哪兒也不甚重要。用葉兆言的話說,“任何有一點歷史的城市都會有這樣古老的、有變化的、有故事的街區”。
上山下鄉、恢復高考、出國潮、下海經商、國企改革……那些推動故事發展的歷史背景,更是一群人的集體經歷。這群親歷過的人,正活生生地在我們身邊,能交流,也能干事。只是,時代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痕跡,也多多少少左右著他們的人生,又牽扯起我們的命運。
這種普遍性使得讀者能夠很輕易地走進作者構建的文學世界,并繼而自身的經歷做鏈接,做延伸,由此及彼。
更重要的是,小說的敘事也保持著平視的角度,說的都是大白話,沒有講什么人生道理、金玉良言,更沒有開出“上帝視角”帶著讀者把起因經過都給說明白、捋清楚。它留白給了讀者巨大的空間,去想象,去思考,去填補那些言而未盡的情節。這是對讀者獨立思考能力的一種敦促與尊重,也是對真實生活境況的模擬——生活的苦樂不盡相同,誰又能指導誰呢?
也許,這也是葉兆言為什么認為《璩家花園》與梁曉聲《人世間》相比,世界觀和文學觀并不同的原因。比起帶有俯視視角、知識分子意味的“人世間”,他還是更喜歡“人間”和“民間”。
02
前不久,有風君懷抱著邀請“大咖”的心情,忐忑地和葉兆言約專訪。過程比想象的順利太多。他認為,這是對出版社出版書的尊重,對記者宣傳書的尊重。又想起早前,他曾在別的媒體訪談時說過這樣兩句話。
一句洋溢著確鑿的自信:“這是我真正看家的書。”
一句微瀾著無奈的卑微:“今天閱讀我作品的人已經不多了,少得可憐。正因為如此,我格外珍惜,珍惜自己還有寫作的能力,還有寫作的機會。”

葉兆言曾做客電視節目《我在島嶼讀書》。圖源 微博
身處在講究效率的今天,耗費好幾年,寫一部長長的小說,把時代寫得舉重若輕,又把人生寫得欲說還休,還有意無意留給了讀者發揮的空間,很難,也很難得。
現在,葉兆言——這位大名鼎鼎的葉圣陶的孫子、知名作家葉至誠的兒子,成長在不折不扣文藝之家的“繼承者”;既在廠子里拿過好幾年鐵鉗,又是終成拿筆桿子過活的“跨界者”;年近七十還保持著“戰斗熱情”的文學圈公認的“拼命三郎”;會跳出來說“純文學從來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大家都這么說,于是也難得有人跳出來揭穿”的”實在人”——誠摯地捧出了一部《璩家花園》。
它值得我們去讀一讀。這費不了多少時間。
03
有風君:《璩家花園》是您現有十四部長篇小說中體量最大、故事時間跨度最長的作品。在這樣一個年紀,耗費精力去投入這樣一部宏大作品的動力是什么?
葉兆言:說不上什么動力。作家就是一直要和“寫不出來”作斗爭,和“寫好”作斗爭。《璩家花園》只是我連續勞作的其中一步,就像運動員一樣打了一場比賽而已。當然,因為隨著年齡大了,體力上會有點跟不上。所以就比較笨的辦法就是增加每天的工作量。
可以明確的是寫作并不容易。都說“便宜沒好貨”,寫得累,寫得不容易這是正常的,藝術就是克服困難。我能接受精力的耗費的“寫不出來”,但一直覺得“寫作容易”是個大問題。
有風君:要怎么理解“容易的寫作”?
葉兆言:因為寫作一旦容易了,就意味著你可能在“駕著輕車走熟路”。這是寫文章的一個大忌。媒體說總說我關注南京、熟悉南京、熟悉民國。這種評價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一種“麻醉劑”。文學創作不應該輕車熟路,一定要有許多“不痛快”“不適應”才有意思。
當然,一個作家也許已經費盡心思變花樣了,在讀者看來可能也沒“跳出去”。但是我必須要有“要跟自己過不去”的想法,并為此做出努力。如果一篇小說沒有讓我覺得有不好駕馭的地方,那就是有問題的。
有風君:您覺得《璩家花園》不好駕馭的地方在哪里?
葉兆言:每一本書都有不好駕馭的地方。要說《璩家花園》有什么不一樣,主要是技術操作的問題。
比如寫民國小說,我畢竟是不是那個時代的人,所以最關鍵的是要把不熟悉的歷史盡可能寫真,要讓讀者覺得“這家伙好像就是那個時代的人”。“真和假”對于讀者的閱讀體驗來說是個很重要的事情。
而《璩家花園》描寫的時間和空間我都太熟悉了。我就想把它弄得跟假的一樣,讓人覺得這故事和我本人沒關系。我其實不希望人們評價《璩家花園》“寫得很真實”,因為它本身就是一部虛構小說。
有風君:把小說寫“真”不好嗎?
葉兆言:小說是虛構的,“真實”不應該是它唯一的評價標準。都說“真亦假時假亦真”,這個“真假”是可以相互作用的。
卡夫卡寫《變形記》,把人變成甲蟲。這事情顯然是假的。但是他把人變成了甲蟲以后感受寫得跟真的一樣,讓讀者能體會、理解、代入這樣一個看似荒誕的故事。文學藝術要表現、要追求的就是這樣一種人的真實處境,而不是故事的真實。
有風君:《璩家花園》主角璩天井很平凡,也有點窘迫,他的人生軌跡也幾乎是“被動接受”的結果。比如,高考恢復,他考上了一個好學校,卻被人隨便一說就沒去讀。但是您很喜歡他。您覺得這樣一種人物的閃光點哪里?
葉兆言:寫小說人物,我當然希望他們身上有閃光點。不過,我覺得璩天井身上可能既有賈寶玉的影子,又有薛蟠的影子,三言兩語說不太清楚。讀者可以自己體會。重要的是我給了他“生命”,就必須要讓他“活起來”。
我清楚地知道璩天井是個理想人物。現代人很少會有人想他那樣去癡迷、踏實、不計回報地只愛一個人。但就算99%的人不是這樣,也還是會有那1%的人存在。璩天井就是這樣一個幸福的人。
有風君:怎么理解璩天井的“幸福”?
葉兆言:說老實話,我一直認為“愛別人的人”和“被愛的人”更幸福。我這段時間在嶺南大學駐校教課,讓同學們寫一封情書。我發現他們最大的問題在于表達的都是“希望別人來愛你”。
有風君:是太“被動”,沒有掌握“主動權”。
葉兆言:這和主動不一樣。他們沒有把那種純粹的天性,單向度的,像陽光射出去一樣那種不圖回報的愛展現出來。
就像我們對子女的感覺一樣,一種單向的,像陽光一樣射出去的純粹的天性。好多年輕人在表達“你愛不愛我,我愛不愛你“。這是一種交易。所以我一直說璩天井是“假”的。我需要在他身上花很大的力氣,讓這一個假的人立起來。
有風君:您希望讀者通過閱讀,成為璩天井一樣理想狀態的“幸福”的人嗎?
葉兆言:完全沒有。現在有個很流行的詞叫“爹味”,是吧?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千萬不要在小說中間“爹味”太重,不要有太多評判在里面,這是很要命的事情。
我比較擔心的是,讀者在閱讀上會有一些困惑。比如璩天井不小心爬上祖宗閣,意外看到女性更衣,感到大為震撼的事情。它反映的是那個時代的真實存在,不是什么低級趣味。我擔心璩天井留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個“不正經的男孩”。
今天,大家的閱讀可能比較粗糙。其實我在小說里面埋了許多需要深究的細節。我還是也希望大家能夠在閱讀的時候,把它們背后的深意給挖出來。
有風君:《璩家花園》面世有一段時間了,也開了作品研討會。對您來說,哪些評價讓您印象深刻?
葉兆言:不能說我很在乎讀者意見,也不能說我不在乎。但問題是我的習慣是一個作品寫完了,得趕緊進入下一階段的工作狀態。我會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人總是很虛榮的”。不要太在意別人的評價。就拿我在嶺南大學做駐校作家來說,我就覺得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每周要講一節課,我得寫講稿。寫完講稿,年紀太大了又背不下來。太累。
當然,有時候也有意無意會看到一些評價。對于那些沒說到“要害”的評價一笑了之就行。也有很尖銳的批評家,真是看到你的弱點,需要嚴肅對待。
有風君:哪些評論戳到您的“要害”了?
葉兆言:有兩個人說的話我經常會想起來。
一個是王朔。當時別人轉給我一篇他的文章,大概意思是:像葉兆言他們那樣的江南才子,日子過得太舒服了。(注:王朔曾在訪談時提到:“蘇童、葉兆言,在南方的生活太舒服了,作協團結一氣,像個大家庭一樣,所以文章有閑適氣、才子氣、六朝氣,小說也就一般般。”)我會把他的話用來提醒自己,不要過得太舒適,不要才子氣,不要自我得意,要老老實實工作,老老實實干活。
還有一個顧彬(注:德國漢學家)。他的很多觀點我是不同意的,但有一句話的確是懸在我腦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他說:中國作家最大的問題就是重復自己。
我總是在提醒自己不要重復自己,我們從事的文學必須是要有追求的,是世界性的。南京作家寫的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而中國文學又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世界文學像高山一樣豎在我們面前,我們必須努力往上爬,不能停止攀登,不能固步自封。
我的興趣并不是南京的“鹽水鴨”和“鴨血粉絲湯”。我永遠不要做一個“賣土特產的”。
有風君:您覺得這個時代,身為一個作家的使命是什么?
葉兆言:使命這個詞太重太大,一個小小的作家怕是擔當不起。作家永遠不要高估自己。魯迅也說過“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我對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認識,老老實實把文章寫好,不要裝,夠真誠,就可以了。
有風君:其他就留給后面人評價。
葉兆言:對。但我也在想,一個作家有時候也挺憂傷的。現在看文學的人不如以前多了,很可能我作品根本到不了別人的眼皮底下。
但就像愛情一樣,就算有99%的人都不再看了,也還有那1%。這種信念還支撐著我,萬一別人有機會看到你的小說,你要對得起別人。
有風君:接下來的新作會做一些創新嗎?
葉兆言:肯定有,這個是毫無疑問。但是我在沒有完成以前先不想說。
有風君:是小說嗎?
葉兆言:當然是小說了。最快出來的大概是在嶺南大學上寫作課程的講稿。從理論上說,課要持續到明年1月。
有風君:會把上課內容整理成書。
葉兆言:其實不是整理成書。我是先寫成書再講。這是最笨的辦法。
 責任編輯:李璐璐
責任編輯:李璐璐葉兆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