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底,北京短暫地褪去潮熱,天氣舒爽。科幻作家、華人科幻協會副會長江波從外地趕來參加一場活動——“匠心筑夢·煥新視界——中國科幻·國漫崛起”動畫行業對談。
一身運動裝,一個雙肩包,江波沒有舟車勞頓的疲憊感,關于科幻的一切話題他都能聊得生動、深入,有問必答,保持開放。江波是典型的“理工男”,2003年,他從清華大學微電子專業畢業,同年發表了首作《最后的游戲》,后陸續發表《移魂有術》《濕婆之舞》《隨風而逝》等眾多中短篇小說。2012年開始創作長篇科幻文學,歷時4年寫出《銀河之心》三部曲,以近百萬字的篇幅展現了巨大時空尺度下的太空世界,獲得第28屆銀河獎“最佳長篇小說獎”,同名動漫改編作品也在科幻迷中引發討論。
一篇小說,一部電影,一部動漫,關于科幻作品的改編創作,關于未來世界,關于人工智能,活動間隙,他和記者聊了起來,身邊不時有人拿著書請他簽名,他對待讀者非常熱情。在江波看來,“說到底,關于創作的所有議題最后都要回歸到人”。
以下,是江波和人民文娛記者的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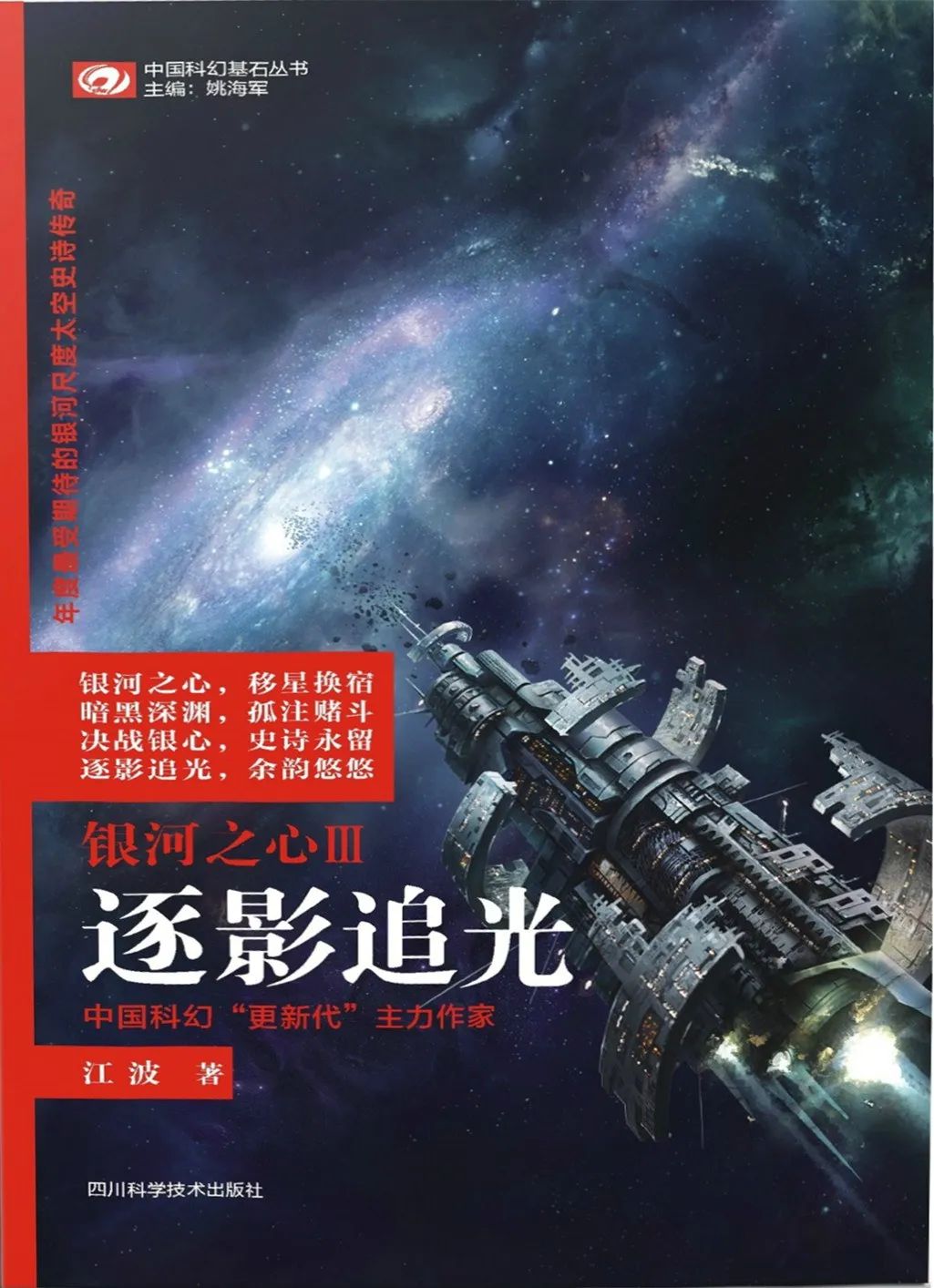
“盡量少去干擾他們的創作”
人民文娛:一直以來,包括科幻作品在內的文學作品影視化對創作者來說都是“驚險一躍”,在您看來,成功的關鍵是什么?
江波:改編的成敗受到很多因素影響,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以我的經驗來看,拋開原有IP本身的影響力不談,主創人員是改編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一個好的主創團隊必須抱有一種強烈的熱情與投入感,這種自信和激情往往能夠支撐他們走得比別人更長遠一點,做得更好一點。
有時候,堅定的信念可能決定一個作品最后的命運。
科幻作品的影視化改編還要看留給創作者的空間有多大。如果一部作品本身沒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它的敘事結構很好,是一個優質作品,這反而給改編者更大的創作空間。這就像,《三體》本身已經是現象級的文學IP了,加上它的世界觀非常龐大,牽一發而動全身,那么很多設計、調整都要配合原著去做,過于大刀闊斧的改編反而不容易成功;反觀《流浪地球》,少數讀者可能讀過這篇中篇科幻小說,而電影的成功才將其轉變為一個影響力巨大的IP,最后,電影反而脫離原著變成了這個IP的主干。

人民文娛:您的長篇科幻作品《銀河之心》也被改編為動漫,您在改編過程中會著重強調作為原著作者的主體性嗎?
江波:《銀河之心》的動漫改編,和小說原本的故事線是有偏差的。在創作過程中,導演和編劇根據需要和經驗自行把握,其實是一件好事。只不過,《銀河之心》是長篇小說,即使是對細節的調整,也需要巨大的努力才能做到把情節圓回來,所以改編難度很大。
影視創作的編劇環節會受到很多限制,是工業鏈條上的一環,并不像作者獨立寫作那么自由。我的原則是盡量少去干擾他們的創作,可以參加一些討論,但不會深度干涉發展的結果。小說改編成了影視,融入了其他人的想法和努力,如果一定要別人遵從我的觀點,那可能有點太霸道了。

人民文娛:您怎么看待影視化改編后“原著黨”不買賬的問題?
江波:這個事情見仁見智。像《冰與火之歌》改編劇《權利的游戲》,一些原著黨的確不滿意,但這并不妨礙這部劇收獲了更廣泛的受眾。
在我看來,影視化團隊如果有足夠的自信認為某種改編方式是好的,就應該按照自己的路子去走,作為創意行業,應該對觀眾的喜好與傾向有自己的判斷。
換個角度想,“原著黨”的討論反而增加了作品本身的熱度,這種爭議其實是良性的,因為它是作品兩種不同形態之間的競爭,也是作者和讀者之間另一種形式的互動。

不必刻意強調中國元素
人民文娛:您如何看待如今中國科幻動畫的發展?
江波:當前我國科幻動畫的興起,一方面得益于科學技術的發展,技術前所未有地滲透到日常生活當中,所以電影、文學、動漫都會受到科幻元素的影響。
另一方面是動漫產業本身的進步。從之前《大鬧天宮》《哪吒鬧海》這類古典水墨動漫的巔峰,后來有一段沉寂,到現在又重新輝煌。在這個過程當中動漫題材擴展到科幻領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以及制作水準的提高,全球影響力的提升都是時代的必然。

人民文娛:不同于西方個人英雄主義的敘事,中國動畫常常出現一種集體敘事,您怎么看待這種差異?
江波:每種文化都有一些核心理念,它們深刻滲透在人的思維當中,所以中國人做影視時也會不知不覺間展現這些理念。西方也有自己的特點,由于宗教的影響,他們的救世主情節非常強烈。但中國人自古推崇“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敘事,這種差異是對價值體系的不同判斷,價值觀念并不是絕對正確或者絕對錯誤的,而是在幾千年歷史發展中形成的。
影視作品相當于我們站在自己的立場來闡述我們的觀念,那這些觀念能夠影響多少人?我們的社會現實會發生什么變化?這個命題其實是很大的,是一種社會工程性的問題。影視作品能夠做的就是把這種理念通過作品潛移默化地傳播給更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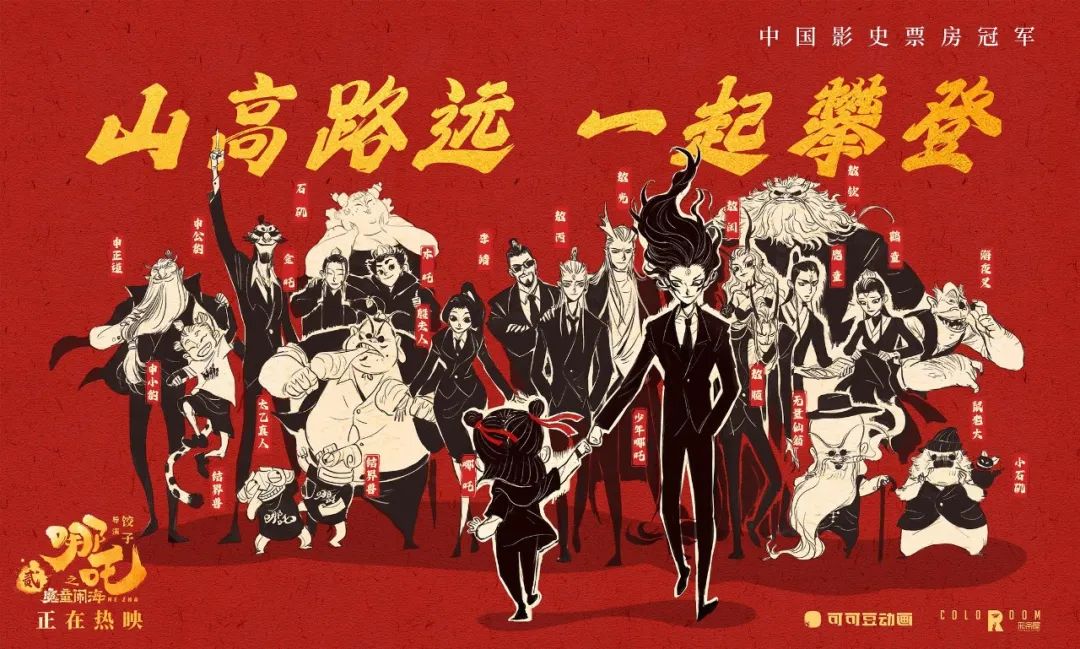
人民文娛: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科幻動畫中有表達空間嗎?
江波:在我看來,并不是只有山水田園才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中國文化也要面向未來,結合現代科技。當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影響力的時候,不能把目光局限在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東西上,還可以看看我們當前有什么,我們能發展出什么,這才叫發揚中國文化。
世界已經是一個“地球村”了,處于彼此影響、彼此交錯的狀態。科技本身就是跨國界的、流動的,世界的未來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當中必然有中國元素的存在,但是不需要去刻意強調,因為我們中國人想象出來的未來,本身就是屬于中國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塑造一個屬于全人類的未來,這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影響力。

太空為什么這么重要
人民文娛:談到未來,您的作品《銀河之心》也是講未來的故事,在您截至目前的整個創作生涯中,這部作品有怎樣的地位?
江波:我一直把《銀河之心》三部曲當作自己的代表作。我的社交媒體頭像就是“銀河之心”4個字,它包含一種寓意——雖然你只是地球上微不足道的一個人,但你的思想可以擴散到整個宇宙。
《銀河之心》的架構非常宏大,不僅僅是這三部曲,還包括一些中短篇,還有一部《紅石》。可以說,《銀河之心》是我對銀河史、宇宙史的想象。人類進入銀河系太空旅行之后,人類文明發展到宇宙3級文明——根據蘇聯科學家卡爾達舍夫的劃分,我們目前處在0.73級文明,3級文明指的是掌握了整個銀河系的文明。這個過程是怎樣的、那時人類是否仍然存在,等等,關于這些問題的浪漫想象都在這部作品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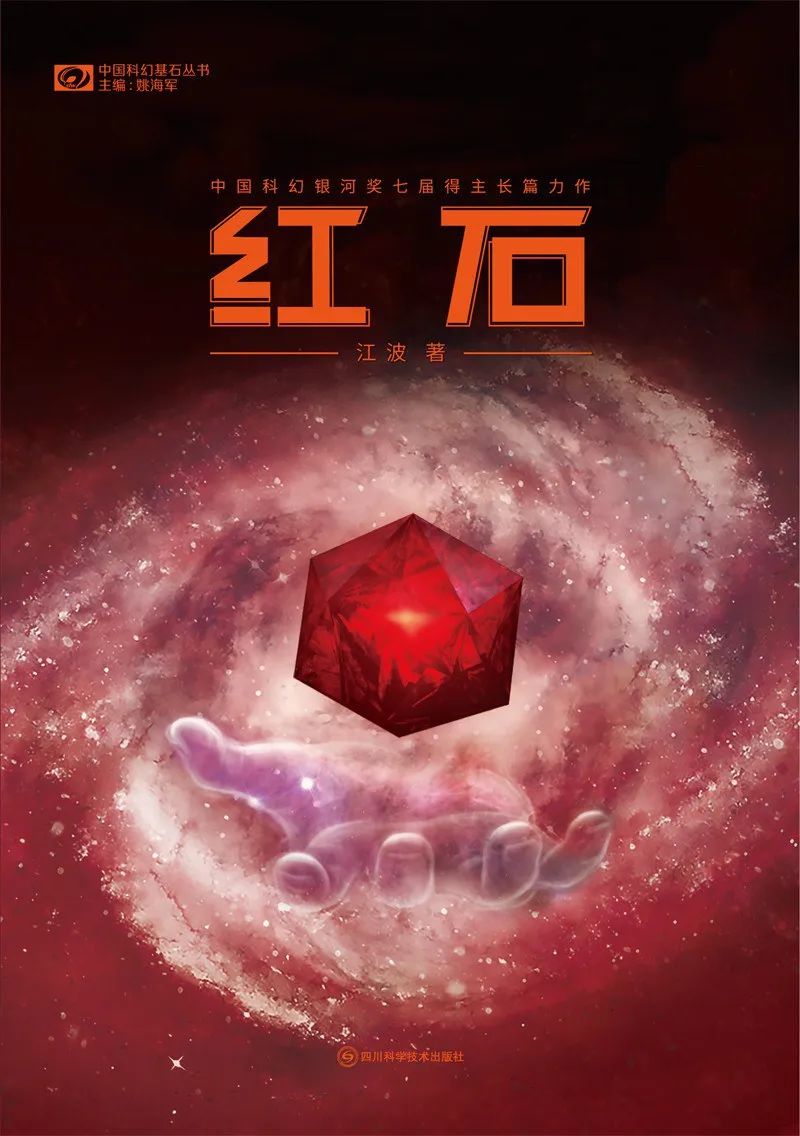
人民文娛:《銀河之心》和您最早創作科幻文學的初衷是吻合的嗎?在成長過程中,哪些科幻作品對您影響深遠?
江波:我最早創作科幻小說的時候,作品主題就集中在太空探索上。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美國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經典長篇小說《銀河帝國》,它講述的是,人類早已建成一個銀河帝國,銀河帝國怎樣陷入混亂,這個混亂又怎樣通過一些人科學理性的認知與方法平息了。它的疆域是整個銀河,時間跨度以十萬年甚至百萬年為尺度,我寫《銀河之心》的時候也設定了這樣的時空跨度。
我一直認為,作家如果在年輕的時候受到某種事物的啟發,未來他在這個方面的興趣會特別強烈。
在我的青少年時代,科幻給我的印象就特別強烈。比如由美國金和聲公司根據《超時空要塞》《超時空騎團》《機甲創世紀》3部日本動畫重新剪輯改編而成的85集長篇電視科幻動畫《太空堡壘》。它1990年被引進內地,當年我整天守在電視機前等更新。我還喜歡科普作家卡爾·薩根,他著名的作品《宇宙》《魔鬼出沒的世界》給我的印象很深刻,恰好也是太空題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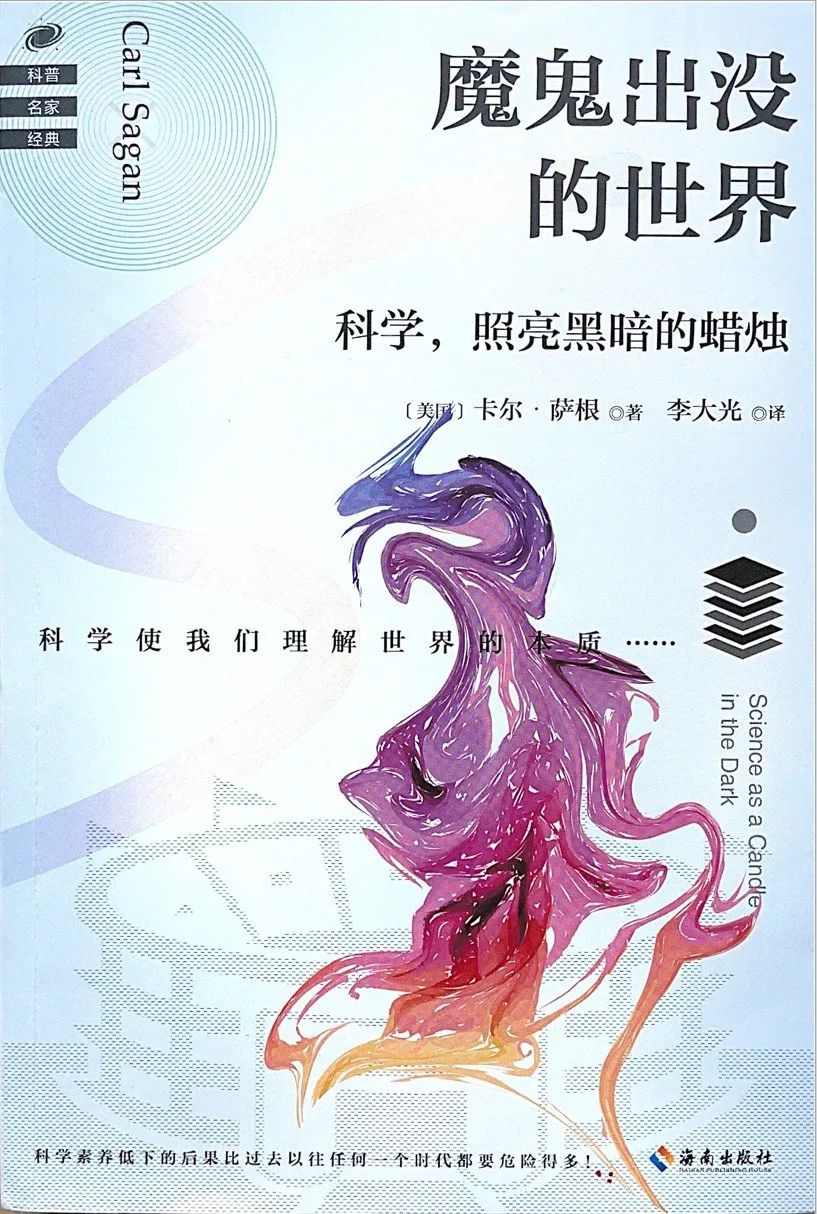
人民文娛:“太空”在您的創作中是不是具有特別的意義?
江波:太空為什么這么重要?原因在于,相對于廣袤的太空來說,地球只是一粒宇宙塵埃。人類如果永遠生活在地球上,其實是有點可憐的。所以在浪漫想象中,我們能從地球走出去,走向一個更加具有想象空間的未來——這是一種非常浪漫的、對人類未來抱著美好期待的想象。
我甚至認為人工智能是人類的一種延續,或者說人類的后代。太空雖然很廣闊,但實際上不適合人類生存,所以將來可能是機器人帶著人類的愿望,以他們自己的形態生活在太空中。
為什么太空在我的科幻創作當中占據重要地位?究其原因,我覺得它是人類的未來,只不過這個未來會跟人工智能深度捆綁在一起。
 責任編輯:李佩藺
責任編輯:李佩藺江波,《銀河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