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勇
1978年出生于上海,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學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碩士、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曾在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世界銀行任職,現任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
去年9月以來,“新質生產力”一詞不斷出現在媒體報道中,迅速被大眾所熟知。2024年全國兩會上,新質生產力不僅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更成為社會熱詞,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7月15日至18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新質生產力再次出現在全會公報中。
“新質生產力不僅是一個熱詞,也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索的新理論概念。”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王勇對《環球人物》記者說。在他看來,加速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形勢使然,更是時代必然。
“因地制宜”特別重要
根據官方給出的概念,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
圍繞這個概念,今年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了10多個產業領域,包括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前沿新興氫能、新材料、低空經濟、量子技術、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
“新質生產力不是農業升級為工業、工業升級為服務業的結構轉型,它更加強調質態,而不是業態。即使是最傳統的農業,如果能通過革命性的技術,進行生產要素的創新組合,也能形成新質生產力。”王勇說。比如傳統農業,如果能通過數字化技術進行選種、育種、種植、收割、深加工,同樣可以構成新質生產力的質態。

2024年4月,在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上,一款“太陽能樹”吸引了采購商。
在已有論述的基礎上,二十屆三中全會又對新質生產力展開了較多新論述,尤其是在具體操作層面。
王勇對《環球人物》記者表示:“新質生產力有三個構成要素,一是技術的革命性突破,二是生產要素的創新性配置,三是產業的深度轉型升級。這三方面都是以科技創新為根本特征的,而科技創新靠的是人才,人才培養又靠教育。因此,二十屆三中全會對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性進行了重點論述,強調‘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
外界普遍注意到,《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改革”一詞被反復提及,出現了50多次。
對于改革的方向和具體內容,《決定》提出“要深化教育綜合改革,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王勇認為,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把經濟領域的“堵點”“痛點”打通、打破,進一步促進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釋放。
《決定》還特別提到“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在王勇看來,“因地制宜”這一點特別重要。去年以來,個別地方在落實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誤以為只有高科技產業才屬于新質生產力的范疇,導致出現不顧本地實際情況,違反本地比較優勢,盲目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現象。
針對這一情況,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絕不意味著放棄或忽略傳統產業,不能一哄而上,不能搞“一刀切”模式。
“目前,傳統產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占比高達85%,而且我們還有很多欠發達地區,當地經濟都以傳統產業為主。對這些地區來說,發展新質生產力主要是通過引入更加先進的技術,給傳統產業提質增效,為傳統產業賦能,同時通過改革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王勇表示,只有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是科學發展的態度,“此次‘因地制宜’正式寫入《決定》,我覺得是非常重要且關鍵的”。

2023年,王勇在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舉辦的國際會議上發言。
“雙線作戰,謀求突圍”
在一些人看來,地緣政治的緊張局面,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前沿技術的限制和打壓,是我國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要原因,王勇認為并非全然如此。
“地緣政治的變化只是外因,發揮主導作用的還是內因,也就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要求。如果沒有中美貿易摩擦,沒有俄烏沖突,我們會不會轉向高質量發展?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粗放型、高投入型的發展模式,已不再符合我國現階段的發展要求。”王勇說,“如果說過去我們要著力解決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問題,那么如今要解決從多到好、從粗到精的問題。”
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國的一些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近年來不斷向外轉移,因此有人擔心中國也會走上美國產業空心化的老路。
對此,王勇向記者闡釋了中國所面臨的“三明治困境”:創新能力更強的國家和地區,比如美國,對我國有壓制效應;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比如越南、印度,則對我國有追逐效應。“中國經濟就像三明治的中間層,前有堵敵、后有追兵,需要雙線作戰,謀求突圍。而突圍的方式包括兩個重要方面,一是通過科技創新進入原本由發達國家主導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業;二是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本國傳統產業提質增效,避免其過早地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避免產業空心化。”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但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中國最重要的還是保持定力。
王勇認為,很多歐洲國家雖然在政治外交上跟隨美國,但在經濟上是不愿意放棄中國市場的,因此中國只有把經濟蛋糕做得更大,內政外交才更有主動性。即使是跟那些主張遏制中國的美國政客打交道,也應該“斗而不破”,盡量團結更多可以團結的人,“當我們的朋友越來越多時,美國想擋也擋不住”。
目前,中國北上廣深和東部沿海的很多地區,已經達到發達經濟體的水平,具備了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等賽道上加速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條件,但更廣大的中西部地區還相對落后,傳統產業的比重依舊較高。因此,發展新質生產力更重要的是運用現代科技對傳統產業進行賦能,提質增效。
“我們既不能錯過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也要警惕一窩蜂地大干快上,違反自身比較優勢發展相關產業,造成資源的錯誤配置、重復配置,這樣反而會損害我們經濟的基本盤。”王勇說,“因此,各地政府清醒的自我認知能力和中央對地方政府考核的科學性,就變得尤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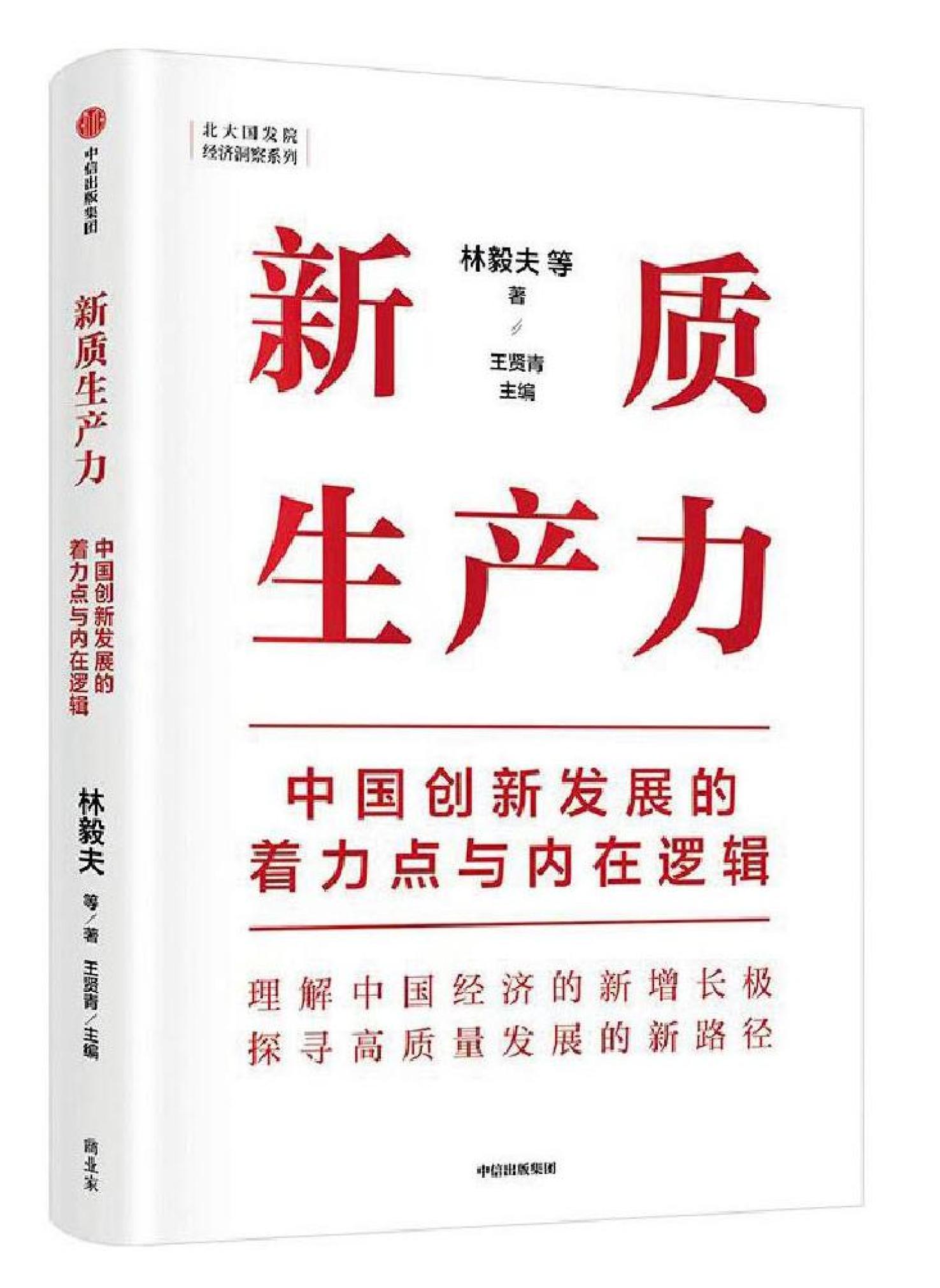
王勇與其他學者合著的《新質生產力》。
中國是“離不開”的存在
對于世界經濟,王勇已經研究了20多年。“國際競爭”這項宏大的課題,不僅是他的研究對象,也是他的親身經歷。
2000年,王勇從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本科畢業,免試直升進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為國家發展研究院)讀碩士。3年后,他又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學位。
芝大經濟系以淘汰率高著稱,王勇那一屆博士生共有24人入學,來自世界各地,都是本國最優秀的學生,但在一年后的博士資格考試中,直接被刷掉了10個人。
留學的6年,王勇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在此之前,即使是備戰高考,他也從來沒有為了完成作業而熬夜,但在芝大,熬夜讀書、看資料、寫論文成了常態。
“班里每個人起初都萬分自信,但一個月的課上下來,男生變得胡子拉碴,有人甚至剃光頭,大家都沉默了,課業壓力無聲地蔓延開來。”王勇回憶道。
當時最難的課程之一是價格理論,為了完成作業,同學們經常熬通宵。王勇至今記得那段“一邊完成作業,一邊看著天空漸漸發白”的日子,“在芝大,不把全身力氣用盡,是拿不到A的”。最終,在這門課的博士資格考試中,他拿了第一名。
芝大經濟系常有研討會,氛圍從來不是一團和氣的,教授們會尖銳地指出對方觀點的錯誤或者不足,甚至有人被逼哭過。當老師們圍著桌子討論時,學生們就擠坐在后面的椅子上旁聽。這種尋求真知、鼓勵創新的精神極大地感染了王勇。
2008年,王勇尚未從芝大畢業,就接到了經濟學家林毅夫的邀請,讓他到世界銀行從事研究工作。當時,林毅夫在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
在北大讀書期間,王勇上過林毅夫的兩門課,還獲得了這兩門課程的全班最高分,之后又跟隨林毅夫寫論文。王勇論文答辯時,林毅夫是其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主席。后經林毅夫推薦,王勇進入芝大經濟系深造,兩人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從2008年到2012年,王勇一直在世界銀行擔任咨詢專家。入職北大前,他還曾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從中國南方到北方,從世界東方到西方,王勇一直走在學術道路上,以中國為起點,又回到中國,用他的話說:“大國逐鹿,都市喧囂,我最喜歡的還是一方書桌、一片寧靜、一份從容,期盼著那一點頓悟。”
多年來,王勇側重于研究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問題。回顧二戰結束以來整個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思潮與現實實踐,他發現,但凡是教條式地套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或是盲目聽從那些看似標準、正確的政策建議,在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效果都達不到預期,甚至比之前更加糟糕。
剛改革開放時,中國的人均GDP還不到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人均水平的1/3,至1994年仍不到后者的平均水平,但現在,中國不僅早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還成功讓8.5億多人脫貧。
這一切使很多西方學者百思不得其解。對他們來說,中國是“看不懂”又“離不開”的存在。即使是一度叫囂要與中國“脫鉤”的美國,過去幾年從中國直接進口的產品減少了,但間接進口的產品不僅沒少,反而更多了。其原因在于,東南亞地區沒有全產業鏈,當地工廠基本上從事的是組裝、加工環節,零部件還是要從中國進口。
“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世界意義。我們基于實踐總結出來的經驗與教訓,不僅可以幫助中國,也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具有借鑒意義。”王勇說,“一些令西方經濟學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中國經濟學家具有‘近水樓臺先得月’之便,只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以規范的方法去分析,就可以給出正確的答案。”
舉報郵箱:jubao@people.cn
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電話:010-65363263
由《環球人物》雜志社有限公司主管、主辦
Copyright ? 2015-2024 globalpeople.com.cn.
版權所有:環球人物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