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大炮放平,當(dāng)槍使!
今天是《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簽訂70周年的日子。
當(dāng)年擔(dān)任所謂“聯(lián)合國軍”總司令的克拉克寫道:“我成了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zhàn)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與李奇微兩位將軍一定具有同感。”
令他們?nèi)绱死仟N的,是“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志愿軍將士。
當(dāng)年的弱冠少年,在世的已是耄耋老者。原屬志愿軍第38軍炮兵團的老戰(zhàn)士蕭模林,耳朵在戰(zhàn)場中被震聾了,接受采訪要戴上助聽器。此外,蕭模林還得與輪椅為伴,他的左腿膝關(guān)節(jié)被美國飛機炸得脫臼,“一走路這腿就掉下來了”。
當(dāng)年在敵人面前,哪怕脫了臼,他的腿肚子從來不會抖。

寫進軍事教材的戰(zhàn)例
“有敵機!大家做好防空準(zhǔn)備!”警戒人員大喊。
當(dāng)時臨近中午,一陣隆隆的巨響籠罩了陣地。憑借多年作戰(zhàn)經(jīng)驗,時任志愿軍第38軍炮兵團2營5連代理指導(dǎo)員的蕭模林覺得不太對頭,這似乎不是飛機的聲音。
他趴在地上,用耳朵貼著地聽,感受到大地的顫抖。他又插上一根木棍,發(fā)現(xiàn)木棍劇烈搖晃。他判定,這個聲音不是來自天上,而是地面!這不是飛機,而是敵人的坦克,距離我方陣地只有兩三公里了。

· 1950年,蕭模林在朝鮮。
果然,沒過多久,美軍一個團以6輛坦克開路,步兵分乘卡車緊隨其后,沿密林間的公路,氣勢洶洶地向我團陣地撲來。蕭模林把大拇指往前一伸,根據(jù)偵察技巧,測出敵人距離我炮兵陣地約600米。
這下麻煩了。“炮兵團的三八式野炮射程9公里,九〇式野炮射程14公里,而且炮彈的軌跡是拋物線,這么近的距離,怎么打?”蕭模林向環(huán)球人物記者回憶道。
還有一個問題。通常,志愿軍炮兵和步兵協(xié)同作戰(zhàn),可眼下只有炮兵。野戰(zhàn)炮是陸軍重要的遠距離火力支援兵器,個頭大、分量重,必須用大量騾馬或者機動車輛拖曳,如果沒有步兵的掩護,幾乎沒有防御能力。
“1951年夏,第五次戰(zhàn)役第二階段結(jié)束后,志愿軍司令部命令我們配合志愿軍第60軍180師到金化南阻擊敵人。當(dāng)我們到達預(yù)定位置時,卻發(fā)生了一個極大的意外——180師受到敵人圍堵不能按時到達。沒有了步兵的掩護,我們團的24門野戰(zhàn)大炮時刻處于危險之中。”蕭模林說。

· 志愿軍火炮手隱蔽在工事內(nèi)準(zhǔn)備向敵人開炮。(受訪者供圖)
撤退?不可能。對待侵略者,就得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同他們對話,這就是以戰(zhàn)止戰(zhàn)、以武止戈,用勝利贏得和平、贏得尊重。
前不久,蕭模林隨部隊涉水強渡照陽江。水流很急,水位可達脖子位置。渡江過程中,能看到一具具志愿軍步兵戰(zhàn)士遺體在江上漂浮著,順流而下。大家都暗暗下決心,一定要為烈士們報仇雪恨。
眼下,炮兵團與敵軍坦克相距只有幾百米了。蕭模林當(dāng)即決定,把大炮放平,當(dāng)槍使!他命令部隊調(diào)整炮口,直瞄前方500米,所有火炮齊發(fā)!敵人還沒回過神來,打頭的坦克就被擊毀,一下橫在了路中央,堵住了敵軍前進的道路。
“這下進退兩難的變成他們了!敵人呼叫空中支援和遠程火炮支援,陸續(xù)發(fā)起10 余次進攻,都被我們擊退。這次戰(zhàn)斗,我們創(chuàng)下了炮兵部隊單獨殲敵1000余人的紀(jì)錄,而我方只傷亡10余人。”蕭模林說。
這次戰(zhàn)斗,連隊榮立集體三等功,蕭模林個人榮立二等功。這場戰(zhàn)斗后來作為經(jīng)典戰(zhàn)例被收進了解放軍炮兵某師軍事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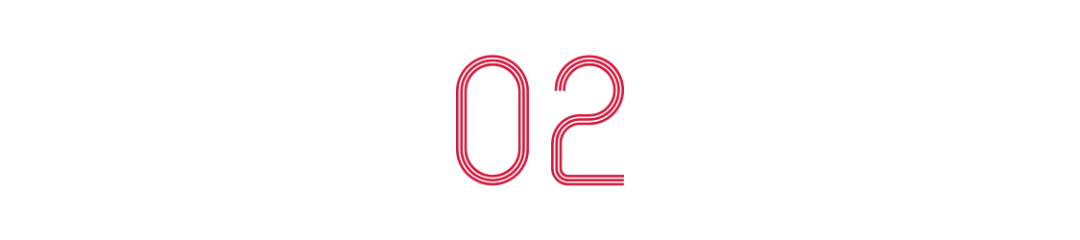
“空中拼刺刀”
1951年1月,在武漢讀高二的陶偉參加了空軍,成為一名飛行學(xué)員。就在當(dāng)月,志愿軍飛行員李漢擊傷1架美國飛機,打破了美國空軍不可戰(zhàn)勝的神話,激起無數(shù)中國青少年從軍報國的志向。
當(dāng)時,陶偉所在班共40人,聽說志愿軍來招募飛行學(xué)員,有30多人踴躍報名,最終20名同學(xué)成功入選。
陶偉出生于1934年9月,當(dāng)時只有16歲。經(jīng)過兩年多的學(xué)習(xí)和訓(xùn)練,他就上戰(zhàn)場了。
“那時候我們技術(shù)不好,我們的飛行員,訓(xùn)練時間只有一兩百個小時,而美國飛行員有一兩千個小時。”陶偉說。

· 抗美援朝時期的陶偉。
1953年5月17日,志愿軍8架飛機升空,與敵人20架飛機展開較量。陶偉掩護長機擊落一架敵機后,開始返航。
志愿軍的米格-15飛機裝載的油不多,能飛的距離有限,只能在朝鮮北部活動,保護鴨綠江大橋和發(fā)電廠等設(shè)施,不能長時間和敵機周旋。
而美國的F-86“佩刀”戰(zhàn)斗機個頭大,裝油多,速度快,是當(dāng)時美國最先進的戰(zhàn)斗機,能飛比較遠的距離。
這次,陶偉在掩護長機返航過程中,就遭到兩架F-86敵機的跟蹤追擊,陶偉和長機幾次擺脫都沒成功。
“他們的時速是1090公里,我們是1076公里,相差14公里。一小時14公里,一分鐘就是200多米,所以每次作戰(zhàn)術(shù)動作擺脫他們,他們?nèi)姆昼娋湍茏飞衔覀儭?rdquo;陶偉說。

· 2023年7月,陶偉在山東濟南接受環(huán)球人物記者采訪。(朱紅羽 / 攝)
得想個辦法。作為僚機駕駛員,陶偉想做出先向外轉(zhuǎn)彎,而后再回轉(zhuǎn)的“S”形動作,支援長機。
10天前,他和長機也曾被尾隨,當(dāng)時敵機是沖著陶偉的僚機去的,長機就往外轉(zhuǎn)彎,但轉(zhuǎn)的角度小了,回來的時候,距離敵機很近,也就是沒有飛到敵機后面,對敵機構(gòu)不成威脅,這樣就很被動。
這一次,陶偉在外轉(zhuǎn)時有意把角度轉(zhuǎn)大一點,飛出去的距離遠一些,這樣回來時,正好飛到敵機后方,敵機成了陶偉瞄準(zhǔn)的目標(biāo)。
遺憾的是,在陶偉轉(zhuǎn)出時,敵機突然開火,長機被敵機擊落,只剩陶偉孤軍奮戰(zhàn)。
他正要為長機報仇時,敵機突然放出減速板,來了個“空中急剎車”,企圖讓陶偉的飛機沖到前面去,成為靶機。前方敵機迅速向自己逼近,陶偉本能地把飛機向上拉起來,打算做一個360度的向左滾轉(zhuǎn)動作。
但是,如果等飛機回到正位,可能就真的成了敵人的靶子。陶偉抓住千鈞一發(fā)之機,在飛機滾轉(zhuǎn)了大約180度時,人還是頭朝下時,就立即開火了。敵機當(dāng)即被擊落。
當(dāng)時與敵機作戰(zhàn),通常是在數(shù)百米外開火。此前空軍英雄劉玉堤在距離150米時擊落敵機,已屬難能可貴。經(jīng)分析,陶偉擊中敵機時,與敵機的距離僅為120米。
在開火的瞬間,飛機上的相機自動拍下了那一刻的畫面。“之后我得跟副師長匯報,副師長邊看膠卷畫面邊聽匯報。他是個老紅軍,也是經(jīng)歷過刺刀見紅的老戰(zhàn)士,一看就說:‘這不是空中拼刺刀嗎?’‘空中拼刺刀’這個詞就這么產(chǎn)生了。”陶偉也被稱為“空中拼刺刀第一人”。
“我們的飛機很多性能比不上美國飛機,唯獨拉升性能較好,所以要多利用這一點。在敵人優(yōu)勢裝備面前,拼的更多是勇氣。敵人另一架飛機看到同伴被擊落,立馬就逃跑了。”陶偉說。
兩個多月后,美國在《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上簽字。“停戰(zhàn)談判從1951年就開始了,打打談?wù)劊瑲w根到底還是靠戰(zhàn)場上的成績說話。歸根到底,中國人要有血性!這股血性和拼搏精神永遠不能丟!”陶偉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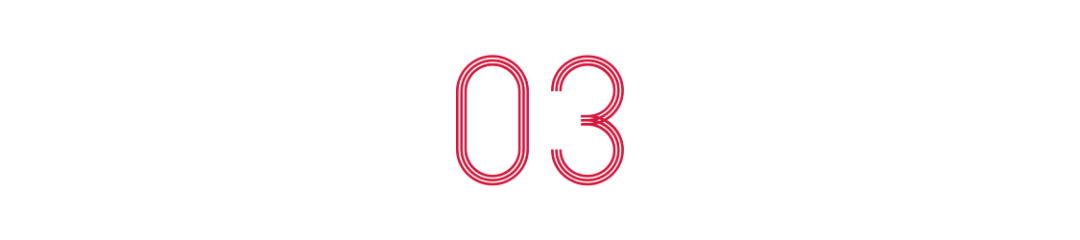
敵人被手榴彈“打成傻子一樣”
1952年10月開始的上甘嶺戰(zhàn)役,敵人的密集炮火把山頭削低了兩米多,巖石被炸成了粉末。
11月1日晚上,副班長蔡興海所在的志愿軍第12軍31師91團8連4班9個人,奉命從金城前線來到上甘嶺597.9高地的9號陣地。蔡興海在地上抓了一把土,發(fā)現(xiàn)里面有3塊彈片,其中一塊還是熱的。
修了一晚上工事,蔡興海既疲勞又有些緊張。9號陣地處在597.9高地的前突位置,可能是敵人首先進攻的對象。
這時,老兵況厚勝遞給他一支香煙,想讓他解解乏。他接過來一看,發(fā)現(xiàn)上面寫著“打擊侵略者”5個字。“一看到這些字,把煙一抽,我就忘掉了疲勞,也不再緊張。”
第二天一早,戰(zhàn)斗開始了。由于班長受傷,蔡興海指揮戰(zhàn)斗。敵人的炮火延伸到陣地后面,蔡興海和戰(zhàn)士們覺得敵人近了,迅速從坑道中爬出來,趴在彈坑內(nèi)準(zhǔn)備戰(zhàn)斗。
他們看到200多米開外密密麻麻臥著200多個敵人。蔡興海一看他們并沒有向上沖,斷定敵人使用的是“假延伸”伎倆,是為了把志愿軍從坑道里轟出來。
他立即命令戰(zhàn)士回坑道里。剛進去,敵人的炮彈猶如雨點般猛烈地襲來,戰(zhàn)士們沒有傷亡。
一輪炮火過后,敵人開始向上移動。戰(zhàn)士們沖出坑道,用手榴彈退敵。敵人又開始使用炮彈,戰(zhàn)士們又進坑道。

· 1952年11月,蔡興海和戰(zhàn)士們在上甘嶺陣地洞口迎敵。(受訪者供圖)
經(jīng)過反復(fù)較量,敵人也精了,一見志愿軍扔手榴彈,就躲進彈坑里臥倒。手榴彈落地后爆炸,只會向上產(chǎn)生殺傷力,威力大打折扣。
這時,蔡興海想到,敵人的炮彈有時在我方陣地上空爆炸,彈片就會向下沖擊。如果有人站在下面,必然受傷甚至死亡。他又想到,手榴彈從拉弦到爆炸,有5至7秒時間。
這時,一個克敵制勝的辦法出現(xiàn)在他腦海里。他喊道:用手榴彈“打空爆”!他一只手握緊手榴彈,另一只手用力拉斷拉火線,手榴彈屁股冒起了青煙。他沒有立刻將手榴彈扔出去,而是把它在頭上轉(zhuǎn)一圈,兩三秒后才撒手。
手榴彈正好在飛到敵人頭頂時爆炸,彈片傾瀉而下,殺傷力達到最大,彈坑里的敵人被炸了個正著。戰(zhàn)士們也把這個方法學(xué)了去。就這樣,敵人一次次被打退了。
很快,天黑了,敵人開始撤退,往山下拖同伴的遺體。戰(zhàn)士們這才出坑道透透氣。蔡興海掏了掏耳朵里的渣土,一掏,很疼,這才發(fā)現(xiàn)耳朵受傷流血了。
最終,蔡興海和全班戰(zhàn)士以3人輕傷的代價,打退敵人7次進攻,殲敵400多人,創(chuàng)造了志愿軍小兵群作戰(zhàn)的范例。
他深藏功名數(shù)十年,直到2019年陜西咸陽退役軍人事務(wù)局走訪慰問時,他才為人們所知。
原來,上甘嶺戰(zhàn)役結(jié)束后,在許世友司令員等頒發(fā)的“第三兵團記功命令”上,6人記特等功,其中蔡興海的名字與黃繼光、邱少云等并列。
上甘嶺戰(zhàn)役標(biāo)志著志愿軍在整個正面戰(zhàn)場完全掌握了主動權(quán)。所謂“聯(lián)合國軍”此后再也沒有對我軍發(fā)動超過營級規(guī)模的進攻。美國四星上將弗里曼在談到上甘嶺戰(zhàn)役時曾慨嘆:“即使沒有飛機大炮,他們也能把我們打成傻子一樣!”
史詩般的抗美援朝戰(zhàn)爭昭示世人,再強大的敵人,在團結(jié)的中國人面前也必將遭到迎頭痛擊!(本文將刊載于8月1日出版的2023年第15期《環(huán)球人物》雜志,點此可提前預(yù)約購買)
總監(jiān)制: 呂 鴻
監(jiān) 制: 張建魁
主 編: 許陳靜
編 審: 蘇 睿
(文章未經(jīng)授權(quán)不得轉(zhuǎn)載,轉(zhuǎn)載請加微信“HQRW2H”了解細則。歡迎大家投稿和提供新聞線索,可發(fā)至郵箱tougao@hqrw.com.cn。)
推薦閱讀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今日頭條

川公網(wǎng)安備5101900200431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