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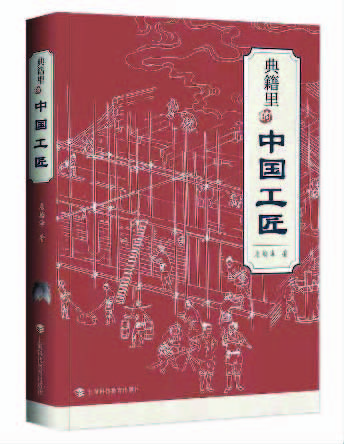
為什么墨子是從工匠中誕生的思想家?你知道自己的姓氏與古代勞動者的關系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日前推出《典籍里的中國工匠》一書,將傳統典籍中關于中國工匠的散見記錄,進行了系統梳理和機趣解讀,在一個個鮮活生動、意趣盎然的科普故事中,中國發明創新之能力和手工技藝之精湛得以展現,“工匠精神”也被更具象化地呈現。
古籍中的工匠們究竟是怎樣的?該書作者詹船海接受了勞動報記者的獨家采訪。
為古代工匠著書:他們創造著人類文明
詹船海告訴勞動報記者,自己從小就崇拜那些動手能力特別強的工匠,認為他們能把器物制造出來滿足生活之需,是很了不起的工作。后來他長期供職于《南方工報》,每天都在進行著弘揚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和工匠精神的采訪寫作,接觸了大批現代產業工人隊伍中的能工巧匠和技術精英,更加深了對工匠的崇拜之情。
當“想寫一本有關工匠的書”的念頭產生,詹船海首先想到的是古代的或者手工業時代的工匠和他們的創造,這不但緣于自己一直以來對文史的濃厚興趣,對進入典籍中的故事和文字有重溫、探究、重述的欲望;最重要的是,“他們(古代工匠)已經進入傳統、進入典籍,是我們來時的路,是我們現代工匠精神和勞動精神的起源。”
詹船海還發現一件事:盡管在傳統典籍中,不缺少向能工巧匠致敬的文本,如《莊子》一書就講述了大量關于工匠和絕活的故事,被奉為百工之神的魯班,民間有關于他的豐富傳說,但與主流的敘事比較起來,這種記載畢竟還只是散見的、零星的,不成規模的。
“說到底,在我們的主流傳統文化中,‘百工'還是個邊緣性的存在,所謂‘士農工商’,其政治地位在所謂的‘賤農'之下,雖在‘商’之前,卻又沒有商人的經濟地位。”詹船海說,“他們曾閃光地存在著,而又被遮蔽著。我們的責任便是讓更多人看見,諸子百家中一直還存在著一家:工家,通過物質的創造,他們也參與創造著人類的精神文明。”
有趣亦有料:姓氏與勞動的淵源
“孔子是偉大的,墨子則是偉大而奇異的。從工匠中誕生的思想家,他是唯一一個。”在《中的手工業》一文中,詹船海語出驚人。在他看來,墨子的兼愛思想像是空谷足音,實則反映了農工勞動者的訴求。“他重物質生產,尊勞動創造。他多從匠作取譬作為論據,并重實驗,從而把弟子們超前地帶入自然科學之王國。”
在不斷梳理資料和講述故事的過程中,詹船海也不吝將自己全新的發現和解讀與讀者分享。關于勞動者與姓氏的淵源,他在《干一行,姓一行》一文中,也有自己的考證:“古云‘工之子常為工’,世代專于一行的結果,就有了自己的姓氏,這就是以職業為姓的形成機制,這很可貴。與天子和皇帝的賜姓于功臣不同,因制陶而姓陶,因攻金而姓段,因殺豬而姓屠,因采冰制冰就姓了凌,因擅建墻籬終得了樊姓,原來都是對勞動的一種命名和肯定。”
“今天我們說‘勞動最光榮’,不光是喊口號,我們的姓氏就是光榮的見證。”詹船海說。
這些“瓜”有點甜:融“科普”于“文史”
不過,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從《尚書》《詩經》、諸子百家,到歷代史傳、類書,或者文學、筆記、志異等,想要從浩瀚文海中,將其間關于工匠發明創造和技藝的記載搜尋、梳理,并有機地串聯起來,并非易事。
詹船海告訴勞動報記者,他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學習、增值和記憶,從一種典籍發現另一種典籍、從一個線索發現另一個線索。“俗話說順藤摸瓜,我自信是摸到了不少‘瓜’,味道還不錯。”詹船海打趣道。最終,各種散見的資料、各種工與匠的故事,都在“勞動和創造”的主題統領之下,梳出了新意:“從宮斗劇中跳出的紙圣”“如果穿越到古代,你該穿什么衣服?”“李白和煉銅工人的偶遇”……單看標題就已妙趣橫生。
詹船海寫作中遇到的另一個難題,是如何掌握書中的“文理平衡”:比如,寫陶土如何燒制成陶器和瓷器,就涉到復雜的化學變化;寫煉鐵成鋼,也要重溫氧化還原反應的知識。
“準確分析化學變化,比直觀描述物理變化就要難了!”詹船海為此查閱了大量資料,甚至把中學的物理化學教材都尋回來重新學習。好在,對于讀者來說,“只要具有中學的物理化學基礎,也就能理解本書所涉及的科學問題了。”
再讀古代工匠:不忘過去、面向未來
除了增長見聞以外,我們今天再讀古代工匠的故事,又有哪些現實意義?在詹船海看來,中國本來是一個不缺工匠大師的國度,但伴隨著快速工業化的焦慮和渴求,工匠們那種精益求精、慢功細活的制作精神,曾幾何時變得有些“不合時宜”。如今,到了中國制造必須追求高附加值的階段,以及對高技術含量、高精密度“大國重器”的迭代需求,中國制造要想走向世界,需要重新正視工匠和工匠精神,工匠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也有待進一步提高。
所幸的是,當現在的人們提起工匠精神,已經不單是指一種手工制作、久久為功的精神,而是指在無論物質生產還是精神創造中,都需要的一種精雕細刻、追求卓越并不斷創新的精神。
隨著工匠精神的弘揚,人們看到精美絕倫的手工制造煥發出新的光彩,也看到“大國重器”不斷升天潛海。
“這說明中國人民越來越有精神底氣了,變得不那么急功近利了;我們現在不僅追求‘有’,而且追求‘優’;不止追求‘富’,更加追求‘強’。這種價值層面的根本改變,正在形成我們新的競爭力,新的軟實力。”詹船海說,“這是一種令人振奮的趨勢,也促使我們不忘過去、面向未來。”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今日頭條

川公網安備5101900200431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