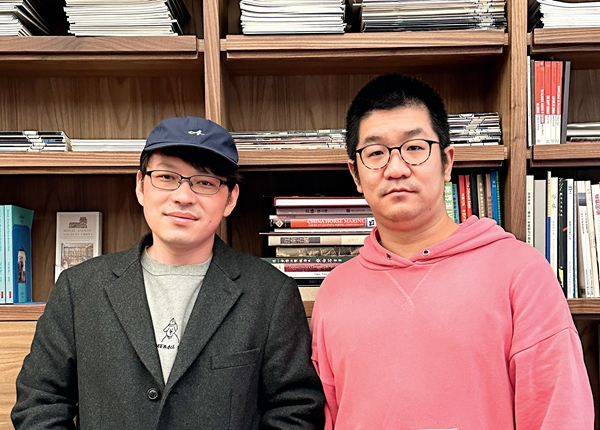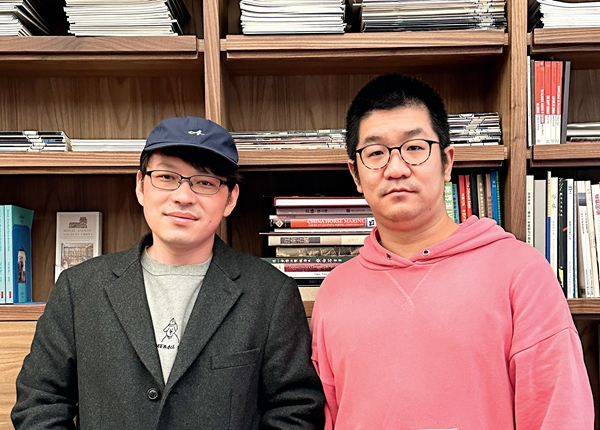
徐明(左)和陳寒松。(本刊記者 王喆寧 / 攝)
徐明:1983年出生于上海,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城市考古”創始人,上海史研究人,文化策展人,紀實攝影師。
陳寒松:1986年出生于上海,畢業于悉尼大學,“上海城市考古”聯合創始人,上海歷史影像及文獻收藏者,中國近代紙鈔收藏者。
11月18日上午,上海地鐵17號線漕盈路站外,聚集了一群等待城市考古的人。他們當中,有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也有來到上海工作和學習的人。其中一人頭戴毛線帽,背著雙肩包,正在將耳機發到每個人手上。他叫陳寒松,是“上海城市考古”團隊的領隊之一。
城市考古,是近年來新興的一種Citywalk(城市漫步)活動,一般有十幾人參與,由“考古領隊”帶領團員游走城市街頭巷尾,了解城市的文化歷史、發展變遷等。
2018年,上海人徐明和相識已久的陳寒松,正式開啟“城市考古”事業。此前,兩人已經有多年城市歷史的調查和研究經驗。從帶隊城市漫步,到辦展覽,再到開設“城考圖書館”,徐明和陳寒松的事業越做越大。
“成立初期,我們就在街上給人們講城市歷史。這是在有限的成本投入下,我們首先能夠做成的事。”徐明對《環球人物》記者說,“之后越來越多人參與進來,尤其在我們做了一些展覽之后,受眾范圍更廣了。”

“城考圖書館”里的小情調。(本刊記者 王喆寧 / 攝)
冷門地點也值得銘記
作為創始人之一,陳寒松幾乎包攬了“城市漫步”活動的所有工作,包括前期策劃、線路選定、準備和講解等。
相較“網紅”的城市行走路線,陳寒松有自己的選擇方向。“我設計線路會優先考慮以下幾點,比如這一地點是否有可能消失、是否平時不太被關注又有內容可講。”在他看來,擁有幾十年歷史的工人新村、100多年歷史的租界區域和擁有數百年歷史的城隍廟一樣,值得被人銘記。
近幾年,郊區逐漸成為陳寒松非常重要的選擇區域。“上海郊區有一些小鎮,或者一些很多人都不知道名字的地方,實際上蘊藏著豐富的故事,但因為不被關注,可能某天被拆除后,再也不為人所知。”陳寒松說。
就在11月,陳寒松新開發出一條“冷門”路線:上海市青浦區有一個鎮子名為練塘,下面有3個非常小的地方,分別叫大蒸港、小蒸和蒸淀。地名都帶有“蒸”字,暗示這3個地方可能有一些關聯。
“很多路線的選擇來自我的長期積累。以前我就知道大蒸港,之后在翻書的過程中有了新的發現。我認為這3個地方是值得開發一條線路的。”陳寒松說。
雖然地點偏僻,但這次活動還是吸引了十幾位團員參與。在青浦的深秋里,陳寒松帶著團員們走過怡然自得的小蒸、安靜悠閑的大蒸港,又漫步于擁有上世紀70年代氛圍的蒸淀,與當年的影劇院、供銷社和綜合商店等合影……
在途中,陳寒松講述了許多從地方志中選輯的精彩故事,比如曹知霸氣開馬路嫁女兒、吳家和顧家的世代血仇等,也解答了有關地名的疑惑——據清代《蒸里志略》記載:“漢濮陽王墓在大蒸東北半里,相傳葬時以酒醋蒸土,其地下不生螻蟻。大蒸鎮、小蒸鎮、大蒸塘皆因此得名。”

2023年11月,陳寒松正在帶隊進行“城市漫步”。
在陳寒松看來,城市考古與歷史相關,也和當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我們要從當下視角切入去看城市歷史,比如風貌保護村,為什么需要保護?在大城市的背景下,哪些元素值得保留?城市考古既是講老的東西,更是對當下的一種觀察,引發人們對當前狀況的思考、感悟。”
談到第一次選擇城市考古路線,徐明和陳寒松的記憶都很模糊。“大概在2018年11月,我們舉辦了第一次活動,前期處于嘗試階段,之后才會提前規劃路線、確定如何講解等。”徐明說。一開始,他主要負責帶隊和講解,陳寒松會穿插幾句。后來,陳寒松很快就全盤接手這項任務。
為了豐富活動講解,讓參與的成員理解城市歷史,陳寒松一直在學習和翻閱資料、文獻。“我自己家里有很多書,也經常翻看工具書,比如地方志,可以按不同層面,找到市、縣、鄉,甚至鎮的志書。對于一般人來講,基本沒有時間、精力、能力去找到和理解書中內容。所以我們的工作就是將晦澀的內容轉譯成好理解的內容,傳播出去。”
在徐明看來,志書就像原石,未經打磨,是展開城市考古的重要原始依據。“如果把專業內容直接講給大眾,有時候是說不清楚的。所以我們需要深入淺出,要精煉、做形式上的轉化,變成社會的、大眾的。這也是我們具備的一種核心能力。”
與城考的淵源
徐明和陳寒松都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都有留學經歷,在從事城市考古工作前已經擁有豐富經驗。
陳寒松上小學時,偶然讀到一本名叫《上海灘野史》的書,從此在心中埋下探尋上海城市文化歷史的種子。在他上高中前,網絡不像現在這么發達,也沒有手機和數碼相機。因為對老房子和城市歷史很感興趣,他翻看了不少課本和書籍,獲得了很多相關知識。
2002年,高一剛結束,陳寒松就出國前往澳大利亞上學。大學時,他選擇了心理學和中國研究專業,碩士延續了中國研究方向。
“我的研究內容也和上海市有關。本科我寫過一篇論文,主題是中國早期流行音樂歌詞中的現代性,也就是1927年到1949年這段時間,講的也是上海。”
2005年,陳寒松開始系統性地關注城市研究。“出國之后,回上海的時間少了。每次回來,我都感覺上海的變化很大,不光是房子被拆掉,很多變化都是不可逆的。”
之前,拍照需要沖洗膠片,對于很多人來講成本比較高。那幾年,數碼相機開始普及。于是,陳寒松拿起相機,走進上海的街道,拍攝和記錄那些可能被拆除的老房子。
在路邊拍照時,經常有人問陳寒松:“你不去拍東方明珠和陸家嘴,為啥拍這個‘破房子’?”“其實,不過十幾年的時間里,上海已經很難找到具有當時時代特色的‘破房子’了。我希望通過拍照,記錄下那些即將消逝的弄堂和建筑,還有局部裝飾、紋樣細節等。”陳寒松說。
日積月累下,陳寒松總結出一套城市考古的方法。“拍照久了會發現一些細節,比如老門牌、建筑上面的字和界碑等。有些已經被破壞了,但把它們作為切入點進行挖掘,會挖出很多和這條街道、區域,甚至城市有關的過去。”
多年來,陳寒松拍攝和收藏了不少上海的珍貴影像,也收集了很多有意思的物件,比如舊紙鈔、舊收據和舊地圖等,積累下龐大的資料庫。在此過程中,他幾乎把上海各個弄堂、拆遷區都走了一遍。
徐明和陳寒松有相似的經歷,很早就到日本留學,之后成為一名文化記者。他受到海外學者提出的“都市考現學”的啟發,學習到當地文化經營的一些做法和思路,為日后創業打下了基礎。
在日本工作6年,徐明越來越無法獲得滿足感。“中國擁有非常多元化的社會,日本給我的發揮空間比較小。從內容本身和文化的豐富程度來講,我更愿意去研究我們國家的文化和歷史。”
當時,國內很少有非官方的人或組織做城市歷史方向的研究,也沒有專門的團隊可以將城市考古做市場化轉化和宣傳。2013年,徐明選擇回國,開始進行城市文化歷史的社會調研,包括走訪拆遷區等。“因為沒有組織性的人力,我能做的事很有限。”徐明說。
“必然”的相遇
在徐明看來,自己與陳寒松的相遇是必然的。“在上海、北京等地,民間自發研究城市歷史文化的圈子很小,我們遲早會認識。”徐明說。當時,兩人在一個朋友組織的講座里相識,發現對城市考古的研究方向和理念相符,價值觀契合,于是決定一起做事,成立“上海城市考古”團隊。
“我們希望讓城市的文化和歷史向社會化轉化。當時,因為以前沒有人做過這件事,它幾乎是空白市場,我們也在賭。上海的文化包容度高,城市具有個性,文化與商業的結合一定能在這里生根發芽。”徐明說。
剛起步時,城市考古活動僅限于“城市漫步”,幾乎沒有人知道徐明和陳寒松究竟在做什么。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認同和支持他們的做法。“當時我對阿松說,如果每次活動有人來,那么這件事就是值得的。”徐明回憶道。
很快,參與活動的人越來越多。首先是從事相關行業的人,比如建筑規劃、社科類的學生,建筑設計和修繕保護的從業者等。他們認同城市考古項目,就漸漸往外傳播,吸引了更多圈外有興趣的人。
隨著知名度的積累,徐明開始帶領團隊擴大事業版圖,如辦展覽、開展館等。2019年,團隊收到上海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的邀約,開啟《蘇州河地名故事》的編纂工作。
為了體現蘇州河歷史的縱深感,團隊花費了幾年時間,經過與專家學者充分討論后,從《水經注》等古籍中梳理了蘇州河的水文地理和歷史演變,包括122個蘇州河沿線的地名遺跡,600多張歷史照片、插圖和古地圖,最終完成了近20萬字的篇幅。
如今,很多開發商會找到徐明團隊進行咨詢,希望街區開發更具歷史文化特色。“我們在一步步往前走,雖然還未取得多大的成就,但至少通過所做的事情,能夠讓一些建筑留存下來,讓更多人了解城市考古。”徐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