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望用我的經歷讓孩子們知道,
讀書真的有用。”
編輯:付玉梅
“我來自四川大涼山,從一個放羊娃成為一名大學生……”
還記得涼山彝族小伙蘇正民嗎?今年6月,他因為6000多字論文致謝引全網刷屏。
在他的講述里,自己的求學之路雖“坎坷崎嶇”但“充滿光亮和希望”。他一一感謝了幫助過他的人,感謝了雖生活艱苦,但義無反顧支持他求學的父母。
“阿蘇唯有繼續努力學習、帶著知識回到大山,幫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
這是他在論文最后作出的承諾。
他如今邁出了第一步。
8月29日,他正式成為家鄉涼山的一名中學支教老師,為同學們上了開學第一課。

“開學第一課”
在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越西縣與蘇正民的家鄉喜德縣毗鄰。
8月29日上午,蘇正民第一次和越西縣第二中學的學生見面。他如今的身份是七年級道德與法治課老師。

·蘇正民在課堂上。來源:中國之聲
穿著一件淡藍色短袖襯衫,他站在看起來狹小、有些許陳舊的講臺上,面帶笑容地望向學生。他好似看見了曾經的自己。
這個新老師難免有些生澀。
“我首先跟孩子們做了自我介紹,然后講解了這堂課的基本框架和一些知識點,告訴大家怎么去學習這門課。畢竟學好課本知識是基礎。”
而對學生來說,講臺上的蘇正民有著更多一重的意義——因為他就是從這里走出去的娃。
“我也是大涼山的孩子,我的起步比大家還要困難”。
“我的小學基礎也不好,初中第一次考試,我就考了班級倒數,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追趕上來,最后順利考上了高中,考上了大學。”
他“風輕云淡”地概括著自己的求學經歷。
剛從村里小學考入城里初中時,他的學習基礎薄弱,考試成績倒數,連講普通話都帶著濃重的口音。班里的同學常常笑他有一把“槍”,叫“彝腔”。
為了盡快追趕上來,他省下生活費用來買學習資料,大聲朗讀背誦課文糾正口音。
后來,他一路考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站在了優秀畢業生代表的發言臺上。那時,再也無人嘲笑他的口音。

·蘇正民。來源:央視新聞
此次支教也是他在學校的項目。他參加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支教團,將在一年后重返學校讀研。

·蘇正民(第一排中)與支教團成員。來源:央視新聞
問他為什么要回來?他說:“如果我們自己都不愿意建設自己的家鄉,誰又來建設家鄉呢?”
課堂上,他用自己的經歷鼓勵初次相見的學生:“只要努力,大家都可以擁有更好的未來。”
山里的孩子們用質樸的眼神齊齊望著他。他們穿著紅色、藍色的校服,背影小小的。哪怕是從側顏也能看出,多數孩子曬得黝黑。
他們校服背后的八個字極為醒目:改變自己,相信未來。
沒有什么比這幾個字更適合他們的“開學第一課”了。
不是全部,但孩子們或多或少能感受到面前的這個老師代表著什么。
“蘇老師上學時要走好遠的山路,現在路修好了,我們都是坐著大巴回家。”學生阿說木加說,他和蘇老師一樣來自大山,但他比蘇老師幸福。
也許,一些種子埋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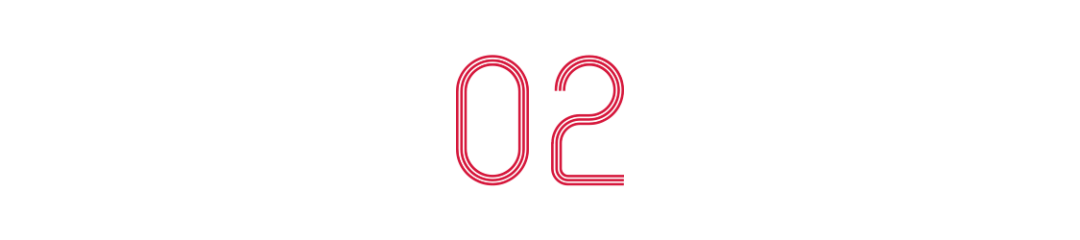
“那條狹窄崎嶇的小路”
我出生在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喜德縣沙馬拉達鄉的一個小山村里,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因為不支持父母的愛情,他們只能到深山里獨自生活。母親懷我的時候,常常只能吃野菜充饑。我從生下來就營養不良,村里的老人常常勸父母放棄我和妹妹,“這么營養不良的小孩是養不活的”。
母親給我取了一個小名“石頭”,她希望我能夠像石頭一樣活下去,希望我能成為一個石頭一樣堅強的人。靠著山泉、野果,我跌跌撞撞地活了下來。
在蘇正民的論文致謝里,自己的人生從一開始就寫上了“難”字。
家里條件差,還要養育三個孩子。父親讀過三年小學、母親不識字。

·右一、二分別為蘇正民的父母,母親懷中抱著的是蘇正民。
但盡管如此,父親還是咬著牙,不想孩子們走他的老路。蘇正民回憶,父親當年是極其嗜好讀書學習的人,他和他的八個兄弟姐妹卻因家境貧寒只能輟學回家放羊、種地。
于是,父親義無反顧、砸鍋賣鐵地把三個子女都送進了學校。
山里的道路,看著很近,常常卻要繞很遠的路,走兩三個小時的山路能到達學校是家常便飯。
雖然還是很難,但蘇正民漸漸找到了一些微光。
小學時他就發現,由于生活條件太艱苦,很多本地老師都選擇了離開。很多來自大城市的支教老師,卻留了下來。
小時候我想不明白,這樣一群皮膚黝黑、衣衫襤褸、渾身散發著汗臭、鼻涕滿臉、連句漢語都不會講的“小屁孩”,有什么值得他們留戀的。我更想不明白,一個艱苦到連當地老師都無法留下的地方,這群來自大城市的支教老師是如何堅守下來的。
支教老師們用點點熒光照亮了我那條狹窄崎嶇的小路。小學畢業后,我有幸進入了涼山州數一數二的中學繼續求學之路。
走到這一步已經很不易,他也曾疑惑自己應不應該堅持下去。
那時,他最大的苦惱就是學不好漢語,很多當地的小孩也因為這個沒有讀成書。
初一的寒假,他打包好行囊,向父母提出了退學,要出去打工。
就如同電影場景一樣,父親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母親掩面痛哭。
“我和你阿達(爸爸)沒日沒夜地辛勞為了什么?我白天打掃大街,晚上還要兼職種地;你阿達白天在磚廠燒磚,晚上還要去種地為了什么?不就是想著你們姐妹三人能夠好好讀書,改變自己的命運,不要再吃我們這種沒文化的苦嗎!”
為了父母,他決定直面難關。
每天下晚自習之后,我就偷偷打著手電筒,用被子蓋住,趴在床上開始學習這些附加的學習資料。偷偷一個人在校園最不起眼的角落里背課文、練習漢語,走火入魔到睡覺時的夢話都在練習漢語。
功夫不負有心人。他的學習成績和漢語水平都突飛猛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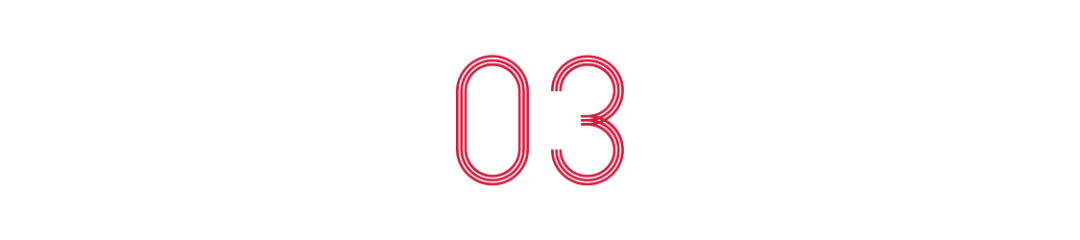
成為播種的人
正當蘇正民以為自己能通過努力讀書走出大山時,積勞成疾的父親離世了。
父親的醫療債務讓這個本就風雨飄搖的家庭雪上加霜。他和家中的姐姐不約而同地決定輟學,留妹妹讀書。只是他沒有選擇外出打工,而是留在祖祖輩輩們耕耘的那片黃土地。

·蘇正民(右)和媽媽(左)、妹妹在參加活動。來源:中國之聲
他沒想到,一個多月后,自己“灰暗的人生”里又迎來了一束光——“涼山孩子們的張媽媽”。

·蘇正民(右)看望“張媽媽”。來源:中國之聲
“張媽媽”名叫張俊蘭,是《天津日報》記者。從1997年開始,她三十多次走進涼山,先后幫助了幾萬個大涼山的孩子。
黨和國家還為我的家庭送來了低保等政策扶持,為我送來了國家助學金等資助。正是在黨和國家以及張媽媽一樣的好心人士的幫助下,我重新坐回了明亮、干凈的教室。
回到校園后,班主任說了一句影響我一生的話:“阿蘇,現在黨和國家、社會上那么多好心人士都這么關心你,給了你那么多的幫助,老師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學會把手心朝下,去幫助其他人。”
這句話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不可磨滅的印記,時時刻刻影響著我。
這道印記始終陪伴著他往后的求學路。
2017年,通過預科招生計劃,他考入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成為當時村里第一個211大學的學生。
背起行囊,他在顛簸的火車中挨過了十幾個小時,終于走出了大山,來到了夢想中的大學校園。但家人和故鄉,一直是他心底的牽掛。
無論身處何處,無論在經歷什么,想起母親,我只有沉甸甸的憂傷。在外求學的歲月里,每當吃到美食的時候,我總會突然地悲傷甚至流淚,我總會聯想到遠方的母親是否又為了省錢,一碗苦蕎、一個土豆就草草解決了自己的伙食。
故鄉的索瑪花又綻開了,山坡上再也沒有父親沉重的腳印,火塘邊只有思念成疾的母親。
從小養成的自卑與沉默,在從未到過的山外世界里更加明顯。他也曾迷茫、惶恐,幸得一路有良師益友相伴。
他想起母親常對自己說的一句話:“別人給我們一碗飯,我們要回饋一袋米。”
于是,作為受助者的他努力成為施助者。
作為2022年湖北青年五四獎章的獲得者,大學四年里,他獻血32次,加入了中華骨髓庫,簽署了器官遺體捐獻協議。

·蘇正民的獻血證。
他還發起助學計劃,募集助學金40余萬元,資助困難學生66名。他組建志愿服務隊,面向涼山留守兒童,提供夏令營等公益項目。

·蘇正民(右一)在支教期間家訪。
他最希望的,是繼續為那座山背后的孩子們做些什么。
他將這些都寫進了論文致謝中。而這6000多字致謝的續集,是他回到了涼山。
“希望用我的經歷讓孩子們知道,讀書真的有用。”開學第一課拉開了他支教一年的序幕。
但在更遠的以后,他依然希望自己能“回到家鄉,回到大涼山”。
這是當年那群支教老師在他心里埋下的種子。
“他們是我最終選擇回到家鄉去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最早的一個種子。它種下了,也生根了、發芽了,不知道能不能開花結果。”
現在,輪到他播種了。
資料來源:央視新聞、中央廣電總臺中國之聲、“共青團中央”微信公眾號、《長江日報》等。
總監制: 呂 鴻
監 制: 張建魁
主 編: 許陳靜
編 審: 蘇 睿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今日頭條

川公網安備5101900200431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