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馮遠征來說,
人藝是他夢開始的地方。
作者:許曉迪 余馳疆
編輯:許曄
馮遠征成為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簡稱人藝)第五任院長,也是人藝70年歷史中第一位演員出身的院長。
這些年里,他的不少影視劇角色都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天下無賊》里與范偉搭檔的劫匪,《非誠勿擾》里的艾茉莉,《不要和陌生人說話》里的家暴男安嘉和……
而他夢開始的地方是人藝。
“我在北京人藝的舞臺上扮演了很多角色,對我藝術生涯產生重要影響的人和事也都是在北京人藝。可以說,北京人藝改變了我的命運。”
馮遠征曾說,人藝是賦予他藝術生命的地方,也是他的藝術歸宿。

從大俗、大雅再到大俗
1985年4月19日,這個日子,馮遠征永遠都記得。
他第一次來到人藝排練廳,參加劇院的復試,主考老師是林連昆。當時考的什么,他全忘了,只記得一進考場,人就暈了,刁光覃、朱琳、于是之、藍天野、鄭榕、英若誠、朱旭……北京人藝所有的大腕全在場。
彼時的他,苦練4年跳傘卻無緣進入專業隊,又錯過了高考,在一家拉鏈廠當工人,上遍了北京的表演培訓班,去北電考試,專業成績前三,卻因為形象一般,“帥不過唐國強,丑不過陳佩斯”,沒被錄取。
所幸柳暗花明,人藝的大門向他敞開。
考入人藝學員班時,馮遠征是班上影視劇表演經驗最多的學生。
1984年,他就拍了第一部電影《青春祭》。電影在云南拍了7個月,導演提任何要求,他都努力做到,學抽煙,學開手扶拖拉機,連續4天沒洗澡,被咬了670多個包。

·1984年,馮遠征出演電影《青春祭》。
“那時,完全靠原始的本能在演戲。”馮遠征對《環球人物》記者說,那可以稱之為表演的初級階段,是“大俗”,沒有技術,只能用真情實感。
馮遠征在人藝參演的第一部大戲是《北京人》。
第一天進排練廳,光是一個撩簾亮相,他就撩了一上午。導演讓他下次來,穿布鞋、梳背頭,借一身大褂,回家以后,吃飯做事都穿著。
從排練廳一出來,他就直奔百貨大樓買了一盒“金剛鉆”牌發蠟,又去“內聯昇”買了一雙圓口布鞋。
他按導演的要求,練習國畫和書法,買了一套《芥子園畫譜》,每天在家臨摹梅、蘭、竹,還買了柳體、顏體的字帖,用報紙疊好小格,每天寫兩張。
為了表現角色修長的手,他留了幾乎一寸長的指甲,經常往指甲上抹點兒香油做保養。
他還向一些行家請教怎么養鴿子,怎么喂食,怎么讓它們自己洗澡……
做完了這些功課,那“一撩簾”才算過了關。

·年輕時的馮遠征。
當表演的經驗越來越豐富,能力越來越強,就到了第二個“大雅”的階段。
“那時是用純技術在表演,該哭哭,該笑笑,演完立刻就收,也挺唬人的。”
2001年左右,有一天坐在片場 ,馮遠征突然特別不高興,覺得自己每天都在用表情演戲。“這場戲是什么?怒,1號表情就來了。那場戲是什么?哭,5號表情就來了。”
而那正是他拍《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的時候。“很多人認為那是我最好的表演,但我知道它不是。”
之后一段時間,馮遠征重新回到人藝劇場,不再接外面的戲,認認真真地用兩三個月排一部話劇。
幾年后,他發覺自己和以前不一樣了,“不僅有成熟的技術,而且有了生活閱歷,已經體會到人間的酸甜苦辣,會從臺詞中尋找情感的爆發點,然后把自己的情感賦予臺詞。這個時候,哭也好笑也好,都是人物的情感”。
這就是表演的第三階段,還叫“大俗”,但本質上已經不同了。
“現在很多演員,演戲時才去體驗生活,或者不體驗,全憑想象……對一個演員來說,觀察生活應該是持續一生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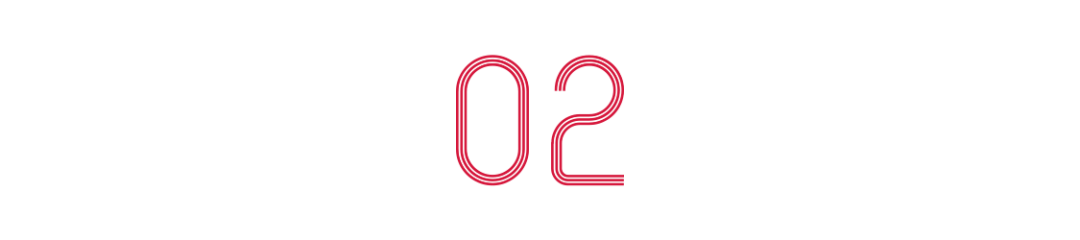
“表演的最高境界是控制”
馮遠征相信格洛托夫斯基的一個觀點:任何人只要智商沒問題,都有成為好演員的天賦。所以,表演老師不是教授者,而是開發者。
他給學生上的表演課也與眾不同。
一個演員接了一個演瘸子的戲,演著演著就忘了腿上有殘疾,馮遠征就拿了支圓珠筆,拿掉筆蓋,讓她把筆頭那部分塞在鞋里,一起身就得硌一下,一邁腿就得瘸著走;
學生們排《雷雨》,演繁漪的孩子表達不出被禁錮的狀態,馮遠征就把她推到空調的木頭罩子里,讓兩個男生頂著,讓她在里面待一會兒,等她再出來,就有了在牢籠里的感覺;
他給“90后”們排薩特的《死無葬身之地》,不解釋納粹和存在主義,讓他們把這個戲當成職場戲來演:想跟老板告密?擠兌死你,他們就秒懂生死險境了……
他教臺詞,跟大部分藝術院校不一樣,不用西方的美聲發聲方式,用的是人藝的方法,用京劇、大鼓、戲曲、相聲來訓練,所以沒有“話劇腔”。
練吐字歸音,他就用一個繞口令“八百標兵奔北坡”,像“紅鳳凰粉鳳凰”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兒”這種都沒用,嘴皮子是松的,“中國話要嘴皮子緊才說得清”。

·2020年1月7日,馮遠征在人藝排練廳。(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當下說一個演員“演技炸裂”,會說他跳不出角色,入戲太深。馮遠征不信,“我演安嘉和,可我沒有回家就打老婆,還是回歸正常的生活里”。
“演員不可能完全沉浸在角色里。在舞臺上,你要控制你的形體、音量、臺詞的節奏、表演的節奏,對方演員忘詞了,要想辦法圓回來;臺下手機響了、孩子哭了,得把這個事情壓下去。拍戲也是,攝制現場不是真空的,你要照顧燈光,照顧攝影機,如果對手演員很矮,還得半蹲著或給他一個臺子站上面。所以,表演的最高境界是控制,不能跑偏。”
表演類的綜藝節目正火的時候,很多人問馮遠征的意見。他說,那就是個真人秀。“我們劇院何冰說得好,如果兩三天就能成為好演員,那還去北電、中戲學習4年干什么?要準備一個角色,不是我跟你探討探討就解決了。”
他給學生上課時舉過《演員的誕生》里一個例子。
兩個演員演《一九四二》的一個片段,演技都很好,哭戲的爆發力也強,但唯獨忘了一點,這兩個人物是在逃荒,渾身沒勁,會把每一粒米都撿起來吃到嘴里,但那個米掉在地上,演員只看了一眼就完了。
“一個演員最重要的就在這個瞬間,是不是顧及到人物最本質的、最基本的先天條件。”

·馮遠征出演電影《一九四二》。
當年拍《一九四二》時,為了演出饑民的狀態,必須迅速減肥,馮遠征、張國立和徐帆幾乎不吃不喝,餓得氣息奄奄。編劇劉震云來探班,張國立就指責他,寫詞寫得太多,真正餓的人是不想說話的。

“人藝絕不是青黃不接”
馮遠征也挨過“罵”。
1999年,林兆華導演的新版《茶館》拉開大幕,人藝拿出了最強的接班陣容,梁冠華接于是之的王立發,濮存昕接鄭榕的常四爺,楊立新接藍天野的秦二爺,馮遠征接黃宗洛的松二爺,吳剛接張瞳的唐鐵嘴,何冰接英若誠的劉麻子。
頭五六年里,他們聽到了不少批評聲。
“老藝術家們已經演到登峰造極,新一代接班肯定會受質疑,觀眾期待的不是王立發、秦二爺、常四爺,而是‘小于是之’‘小藍天野’‘小鄭榕’。所以我們站到臺上,他們會說‘不像’——梁冠華那么胖,于是之那么瘦;馮遠征那么高,黃宗洛那么矮。”

·2005年,《茶館》演出現場,濮存昕飾演的常四爺(左)與馮遠征飾演的松二爺。
但后來,新版《茶館》也成為新的經典,一票難求。
2018年6月,《茶館》迎來了第700場演出,蜂擁而至的祝賀聲中,當年的小梁、小濮、小楊、小馮,也到了老藝術家們告別舞臺時的年紀,北京人藝新一輪的更迭換代正在開始。
“以前,我只想著演戲,反正天塌了有老的頂著,地陷了有小的扛著,我在中間挺自在。但后來突然發現,濮存昕也退了,楊立新也退了,怎么辦?只能我撐起來了。”
但面對一些人說人藝的演員“青黃不接”,馮遠征并不同意。
“他們一定也會經歷幾年被人家不認可,說他們不是濮存昕,不是楊立新,不是馮遠征,但是5年、10年以后,可能觀眾又認為這一代《茶館》真好。所以我們看眼前似乎覺得人藝是不是青黃不接了,其實不是。人藝一直有人才,新老交替一定會存在認可和不認可的過程,但是它一定還是中國最好的劇院。”

·2020年1月7日,馮遠征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人藝的排練廳里貼著四個大字——戲比天大,再大的角兒在這里也只是一個演員。
1987年排練《秦皇父子》,主角在前面排戲,馮遠征、吳剛等一幫學員演士兵,在后邊看激動了,說悄悄話。只聽演秦始皇的鄭榕一聲:“誰在后面講話,滾出去!”舞臺監督立馬將這幫孩子從排練場轟了出去,在樓道里罰站。
30多年后,當年被轟出去罰站的馮遠征,成了人藝新院長。
他說,自己會繼續堅持人藝“傳幫帶”的傳統,讓更多的年輕人在舞臺上成長起來。
總監制: 呂 鴻
監 制: 張建魁
主 編: 許陳靜
編 審: 蘇 睿
(文章未經授權不得轉載,轉載請加微信“HQRW2H”了解細則。歡迎大家提供新聞線索,可發至郵箱tougao@hqrw.com.cn。)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今日頭條

川公網安備5101900200431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