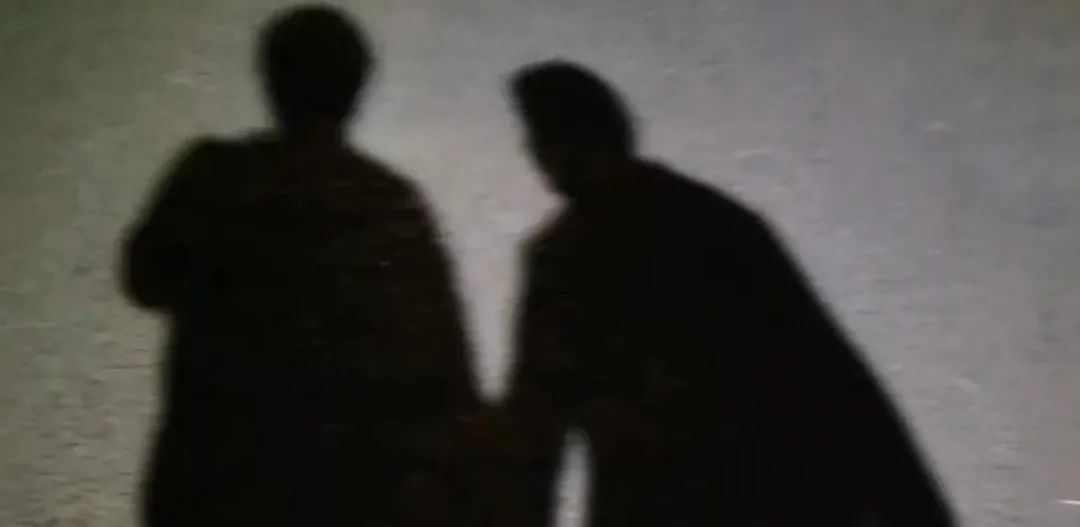
時間把她變成了一個孩子。
作者:劉舒揚
去年8月,柳文(化名)一家又向北京的東部邊界靠近了20多公里——因為“媽媽總是走丟,我們找了個帶院子的房子”。
從小院向東走幾分鐘到潮白河,隱約可以望見對面的燕郊。
當《環球人物》記者走入客廳,柳文的母親上前問候道:“是不是小華的妹妹?你媽身體挺好的吧?”——兩年前,71歲的她被確診為中度阿爾茨海默病。
我們三人圍坐在一張四方桌前。日光彌漫,魚缸里的魚在緩慢游動,電視機偶爾傳出激烈的槍戰聲。老人時而被記者和女兒的談話吸引,時而緊盯電視畫面,或者扭頭,怔怔望著窗外。

·陽光透過窗戶照射進來,白色桌子上擺著柳文做的插花。劉舒揚/攝
學者陸曉婭在照顧自己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的母親時曾寫道,“媽媽正一天天地從這個世界撤退”。
柳文母親的記憶之海也正在經歷退潮。73年的漫長時光隱藏在她不完整的表達中。
只是,老人在談到自己曾靠做豆腐維持家計時,卻緩慢而清晰地說道:“想他們念出書來……最痛苦的時候……是孩子沒上大學的時候。”
關于母親這幾年的生活,柳文講述了更完整的故事。它不止記錄了一對照護者與被照護者,也記錄了兩代女性在彼此身上尋求“如何自處”答案的努力。
以下是柳文的自述。

崩潰
我媽媽是在2020年11月被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病的。其實在那之前,我就有所察覺了。
2018年七八月份,距離第一次腦梗發作10年后,媽媽再次突發腦梗。好在搶救及時,她恢復得很不錯,腿腳什么的,沒留下后遺癥,跑起來我都追不上。

·柳文的媽媽,今年73歲。(受訪者供圖)
但這次發病是個分水嶺——從這以后,她開始鬧了。往往很小的一點事情,她卻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言行舉止都像在抗議:我不滿意,我對你極度不滿意!
媽媽的生日在夏天。2018年那段時間我特別忙,霹靂噗嚕的,既要照顧上學的孩子,還要打理家具定制生意,真是腳不沾地。那天早上出門前我還提醒自己:今天是媽媽生日。可忙一天回來,我就把這事給忘了。
但是媽媽沒忘。于是,她把自己的憤怒如數宣泄在筆記本上,寫了一首打油詩:老媽生日無人問,養兒育女多辛苦,兒女都有“絕戶”日。
我特別委屈。自打2004年把媽媽接到北京以來,我每年都給她過生日,唯獨那一年,是真的忙忘了。
那個時候,我一直以為媽媽這些反常行為是她眼底的黃斑在作祟。我查過,這個病無法根治,病人會出現類似“作”、鬧的行為。可沒想到,這只是開始。
2019年,女兒小學畢業,我和老公商量搬回自己家的房子住(此前為方便女兒上學租住在學校附近)。但那兒離公司不算近,媽媽一個人在家,我不放心。
我們在北京周邊的鎮上找了一棟商住兩用樓,租了一個復式,樓下做生意,樓上睡覺;又給媽媽租了一個50平米的一居室。每天我們去媽媽家一起做飯、吃飯。
起初她狀態還不錯,可能因為有了獨立的生活空間,覺得自己住挺好。但是呢,后來我發現,媽媽開始找不著家了。
她住的公寓樓每層有兩條走廊,方向正相反。她常走錯,去對面敲門,敲不開就罵人家;甚至會把家里大門反鎖,不讓我們進去。她自己在屋里頭,我們也擔心,很著急很著急。
我想,媽媽是不是在城市里待久了憋屈得慌?恰逢女兒暑假,我們全家自駕去內蒙、甘肅、青海、新疆玩了一圈,一共20多天。旅途中她很開心,可回來之后,她的情形反而加重了。
我們不敢再讓媽媽一個人住,一家人搬進了大一點的房子,一樓兩個臥室住人,二樓辦公。這個時候,她開始偶爾半夜跑出家門;后來發展到趁你一會兒看不著,“噌”一下跑了。
我幾乎每天去物業調監控、報警,或者接到人家的報警——媽媽常跑去附近的企業搗亂;要不就到路邊停車處,挨個拽車門。她也經常半夜煮一大鍋粥,說送去給某某吃,又說家里來客人了,總之就是整夜不睡覺。

·被媽媽熱了不知多少次的饅頭。(受訪者供圖)
我有個女同學和我們住在同一個小區。結果,我媽天天半夜跑到我們樓上辦公的地方“抓人”,說人家和我老公在一塊,還跑去罵人家。哎呦,給我老公氣的,跟她也說不清楚。
晚上不開燈,樓梯又那么陡,萬一媽媽摔著怎么辦呢?
我另一個好朋友的母親也住附近。她和我媽關系還不錯,經常結伴出去遛彎兒。有天兩人可能是發生了一些不愉快,打那以后我媽就不斷地打電話、發微信罵人家。
那陣兒真是沒法弄,你出門后不知道回來她又變成什么樣,我們天天掙著命一樣地生活。
2020年1月前后上大凍,下著大雪。家旁邊一個公園沒人,我爬到一個二層高臺的頂上,嚎啕大哭,真的沒辦法,實在承受不住了。
我媽天天咒我罵我:你離婚了,你攤官司了,你蹲監獄了,你老公出去混了……有時帶她出去散心,看著還挺正常的,逛一圈回來,上車之后又問你:你官司打咋樣了?你老公在監獄還好嗎?但其實我老公是個很好的人,我們感情也很好。
2020年前半年,我整個人都是幾乎崩潰的狀態,一天不吃不喝,坐在電腦前面,重復同一個操作,無法控制地流眼淚。
11月我去了一趟海南,想著先去看看情況,如果春節疫情好一點呢,就帶媽媽一起過去。那六七天里,她整宿整宿地給我打電話、發信息,不停地罵。
我再見到她時,她已經近乎歇斯底里了。去醫院做了測試,做了核磁,就這樣確診了,是中度阿爾茨海默病。

“孩子”
拿到診斷結果的時候,說真的,我的心里反而好受了一點。所有的事情找到原因了嘛——她是生病了,所作所為都是身不由己的。這么想,我也就不那么生氣了。
我媽媽是山東人,24歲遠嫁到黑龍江北大荒。她重男輕女思想比較重,我還有一個弟弟。從小到大我一直很努力,就想讓她說我一個好,但她從沒說過。
上世紀80年代,我父親下崗,她在北大荒做豆腐養家,手藝特別好,干倒不少人。我收到大專錄取通知書后,她跟我說不會供我。我剛準備自考,父親生病了。
我開始工作掙錢,2002年來到北京,稍微穩定一點后先把弟弟帶出來。他現在在北京穩穩當當上個班,挺好的。
2004年左右我條件好了一點,就把媽媽接到身邊。她年輕的時候吃了太多苦——東北的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滴水成冰,她在外面賣豆腐,手經常被凍出口子;路面特別滑,身上摔得青一塊紫一塊。我想讓她享享福。
開始她還想繼續賣豆腐,我說別干了,我現在有能力養你了。從我沒結婚,到我結婚、生孩子,不管我走到哪,我都帶著我媽媽,她就是我的一部分。
所以她發病罵我那會兒,我真的特別特別不理解,想著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前世今生”,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緣分”?為什么讓我受這種折磨?為什么我拼盡了全力,就是得不到她一個認可呢?
確診之后,我試著重新認識她,也試著重建我們之間的關系。我發現,那些對她來說重要的事,都隱藏在她的言行中。
比如我有過一個哥哥,一歲時夭折了。她時常叨咕那個孩子的名字,或者跑出門,說我去找我的孩子去。去年有一陣,本來好端端坐著,突然哇哇大哭:“孩子不會說話了!”
再比如,她跑出去時會回頭觀察——看你們追不追我。她渴望得到關注,因為缺乏足夠的安全感。媽媽從小被拋棄,我姥我姥爺就把她領去了。那時她四五歲,也記事了。
現在她糊涂時會說,剛到你姥家的時候,喊你姥“娘”,你姥說“誰是你娘啊,我可不是你娘”。可她清醒時,從來不承認自己不是親生的。曾經老家有個親戚,去世前想和她說這事,她壓根不聽。
我們在東北的時候家里也挺困難,但是她都會給我姥我姥爺錢。真是一輩子都想證明自己,一輩子要強,心強。
有一天天氣挺好,我給媽媽剪頭發,剪到一半她拿鏡子一照,罵我剪得難看,氣得不行。我就想起小時候媽媽給我剪頭發,我也覺得難看,哭了一天。
時間把她變成了一個孩子。

·飯后,柳文牽著媽媽的手一起散步。(受訪者供圖)
現在我也拿她當孩子,當成孩子了,有些問題就不再是問題。罵我一頓我也挺高興,有個媽媽罵兩句還是好的,總比想被罵都沒有強吧。半夜我睡不著,躺在她身邊,就覺得特別踏實,握著她的手,很快能睡著。
有媽媽在,我就覺得總有一盞窗后的燈光為我而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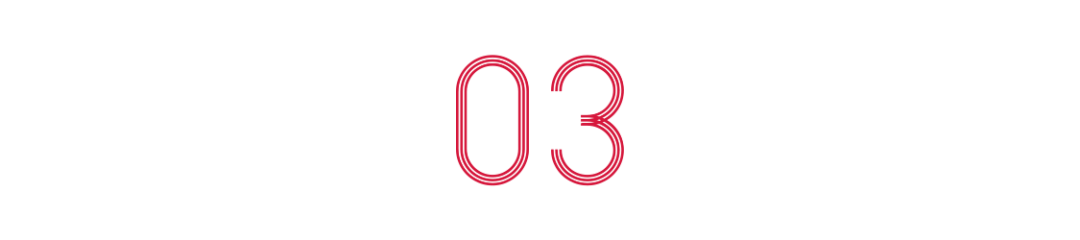
療愈
目前媽媽的基本生活還能自理,起居不太需要我們照顧。我們早上六七點鐘起床,八九點鐘吃飯。然后她玩積木、看電視,我處理工作上的事情。去年開始,我學了配音,在家就能干,也能有一份收入。
她總想幫你忙:在一鍋米飯里加上雞蛋加上菜,說要烙餅,那根本沒法吃;包餃子,我轉個身的工夫,她就去攪和,沒轍;吃完飯她搶著刷碗,常常不洗直接收起來,我不讓她動,她還特別生氣,覺得自己沒用……所以,有時候掃地呀、拖地呀,能干就讓她干。
我也不太考慮以后的事情,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當下。
1998年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媽媽當場就傻了,但是家里不能沒有主心骨啊,所有事情包括后事都是我料理的。
后來我姥我姥爺去世,我又眼睜睜地看著老人咽氣。經歷了這些,我經常問自己,如果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你會怎么過?
我的想法就是不要留遺憾,能做的時候全心全意去做,真到了面對死亡的那一刻,也會坦然許多。
現在我坐在這里看看魚,能傻樂半天;去撿兩朵花,整個枯樹枝,插一插。這就是心態上的調整。

·客廳里的魚缸,擺在餐桌旁。劉舒揚/攝
有人問,你不怕把自己消耗殆盡嗎?
我想,要我因為照顧媽媽而放棄自己的人生,我做不到。人活著,自我成長肯定要有的。只是別人可能每天有8個小時用于提升自己,我只有3個小時,那我就做這3個小時的努力唄。
別人走三步的時候,我只能走一步,是慢了一點,但只要是在往前走的,就好。
總監制: 呂 鴻
監 制: 張建魁
主 編: 許陳靜
編 審: 蘇 睿
(文章未經授權不得轉載,轉載請加微信“HQRW2H”了解細則。歡迎大家提供新聞線索,可發至郵箱tougao@hqrw.com.cn。)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今日頭條

川公網安備5101900200431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