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拍就拍大片!”對記者講起自己歸國后計劃拍攝的首部電影《刀俎魚肉》,上海導演胡雪楊自信十足。他手里有已經(jīng)完成的5000字劇本大綱,這個描述上世紀40年代在上海發(fā)生的諜戰(zhàn)故事在他腦海中醞釀已久,脈絡(luò)愈發(fā)清晰。
三十多年前,胡雪楊是北京電影學院89屆導演系第一個拍電影的,也是“第六代導演”的提出者。海外漂泊多年,如今重回故土,他想用一個精彩、好看的上海故事讓觀眾看到上海城市文化發(fā)展的深厚積累,“它會是一部富有人性光輝,又能鼓舞青少年的商業(yè)大片。”

不想讓1940年代上海成為“戲說”
《刀俎魚肉》的時間線從1941年珍珠港事件開始,到1945年雅爾塔會議結(jié)束,講述地下工作者在上海與西方列強、日軍侵略者、國民黨、汪偽政權(quán)等勢力斡旋斗爭,為贏得中華民族利益殊死拼搏的故事。
胡雪楊是個會講故事的人,和記者描述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情節(jié)時,他的眼睛好像已經(jīng)看到了畫面——
百樂門里,一場盛大的舞會卷入敵我雙方對峙的腥風血雨。鏡頭晃過冰冷的槍口,子彈從包裹在旗袍下的舞步中穿梭而過。特寫里交織出現(xiàn)的是時尚的口紅式樣和講究的咖啡喝法。
生于上海、長于上海,胡雪楊對上海有一種特殊的情感,他不滿于那些“抗日神劇”對上海做了太多戲說。“上海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遠東文化中心、金融中心,東京的人會看上海的報紙,《玫瑰玫瑰我愛你》能唱到好萊塢,那時候的上海聚集了幾乎所有的文化名人。上海是城市文明頑強根植的地方,作為上海人,我有責任拍一部真實還原當時上海城市文明生活的電影。”
大綱完成后,胡雪楊已經(jīng)開始勘景。他不想在車墩搭景,而是尋找符合年代氛圍的歷史建筑。他預想電影中會有大量戲份發(fā)生在酒店里,特地搬進了始建于1926年的金門大酒店體驗生活,一住就是兩個月,每天在各個樓層里爬上爬下,琢磨鏡頭如何在老式建筑的空間里移動。
上生新所的泳池也是他早就計劃好的取景地。胡雪楊想把心心念念的一幕戲放在那里拍——藍色的水面下,血色霧氣般彌漫開來,烘托出一場驚心動魄的緊張廝殺。
他記得有一部英國電影在表現(xiàn)緊張感時,突然一口鐵鍋從高處落下,被追逐的人死死扒住鍋沿,防止鐵鍋震動發(fā)出一絲聲響,觀眾的心也仿佛被提到嗓子眼。他很佩服這種含蓄、深刻的鏡頭語言,打算將其融入自己的作品。“我想拍讓觀眾緊張到喘不過氣的電影。”
演員必須符合人物,必須下生活
《刀俎魚肉》融合諜戰(zhàn)、愛情、懸疑等多種類型,在胡雪楊看來,一部賣座的商業(yè)諜戰(zhàn)大片具備兩點要素,第一,導演、劇作扎實的基本功;第二,優(yōu)秀的制作團隊。他心目中已有名單:來自電影學院科班畢業(yè)的導演、攝影、錄音等主創(chuàng)團隊,和來自上影的專業(yè)化妝、置景、煙火、道具等基礎(chǔ)工作人員。
志同道合、理念一致的創(chuàng)作班底,能夠為電影提供技術(shù)層面的保障。至于演員,胡雪楊還沒有確定人選,但也有標準:“我要找符合角色的演員,有明星出演當然好,但絕不能是沒有演技的流量。演我的戲,任何演員都要下生活,不能串戲。如果做不到,多大牌都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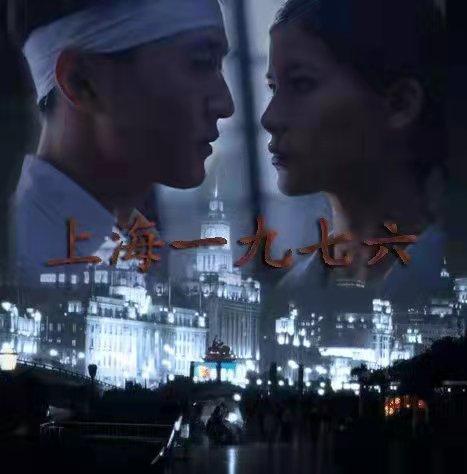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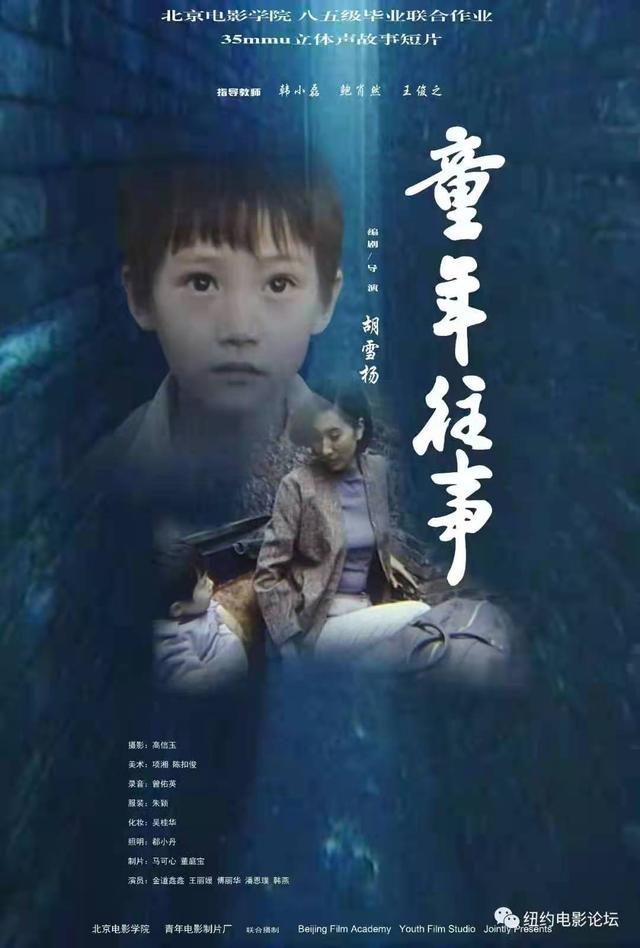
談起演藝圈的不正之風,他深惡痛絕。2015年,胡雪楊受邀回國拍攝一部電影,逗留近9個月,眼見演員片酬從5000萬元被抬到2個億。
“片酬有必要這么高嗎?”他想起自己上世紀90年代拍《留守女士》時,1500元的導演酬勞扣掉差旅費,到手的只有200元;演員片酬同樣不高。
這部電影后來獲得第12屆金雞獎最佳導演處女作,以及第16屆開羅國際電影節(jié)金字塔金獎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員等多個國內(nèi)外獎項,“看,拿200元也能拍出好電影。”
胡雪楊認定“導演中心制”,他認為,各種藝德缺失現(xiàn)象與近年來流行“演員中心制”造成的問題有關(guān)。
1995年拍攝《牽牛花》的時候,有人鬧脾氣罷演,當時電影已經(jīng)拍了三分之一。胡雪楊臨時組織劇組開會,告訴大家,電影還是可以繼續(xù)拍下去。比如要表達“哭”時,可以用替身拍一個抽搐的肩膀、兩只顫抖的手,拍雨水從天上滴落。他覺得電影是鏡頭的藝術(shù),導演總有辦法完成自己的作品,但當這些權(quán)力移交到演員手里,反而為一些人敷衍了事大開方便之門。
下生活、不串戲,是他在選擇演員時對“藝德”的要求。“電影里最重要的是人物,我們想把人物寫透、寫實。用明星陣容,可以‘人抬戲’;但如果劇本、角色好,就可以‘戲抬人’,這才是我們想要的結(jié)果。”
重新定義“第六代導演”
北京電影學院89屆導演系人才輩出,王小帥、婁燁、張元、胡雪楊等人后來被稱為“第六代導演”,而提出這個名稱的正是胡雪楊。
1990年,婁燁在拍攝自己的處女作時,找到同班里最早拍戲的胡雪楊幫忙宣傳。兩人都是上海人,胡雪楊的父親胡偉民、婁燁的父親婁際成還是上海青年話劇團的同事。“當時他有篇宣傳文案,我?guī)退⒄{(diào)了一下,最重要的是加了一句,第五代導演以后,89屆導演、攝影、錄音、美術(shù)、文學五個班的同學是中國電影的第六代工作者。”胡雪楊回憶,自己當初冒出這個靈感,是想到陳凱歌、張藝謀等第五代導演1978年入學后,1982年到1985年之間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沒有招收過學生,等到胡雪楊、婁燁這一屆學生畢業(yè),已經(jīng)隔了一代人。
“當時年少氣盛,好在1990年發(fā)出這句狂言后,1991年我便拍了《留守女士》,1992年又憑它獲了多個大獎,有作品可以托著。”胡雪楊覺得,換作現(xiàn)在的自己,也許不會說出這句話,但當時這篇文章被上海多家藝術(shù)、電影雜志全文刊載,“第六代導演”一詞也傳開了。
“現(xiàn)在看來,這個提法未必合適,從電影藝術(shù)本身的特征來說,第五代導演的構(gòu)圖方式、美學方式都很像,而第六代導演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看我和婁燁的作品,也許大家會以為是兩個班的學生,我們自由、隨意的藝術(shù)風格很難用‘一代’去概括。”
很多人覺得第六代導演電影偏向于獨立和個人化表達,胡雪楊認為,長年的藝術(shù)電影教育熏陶導致許多電影學院畢業(yè)生都從拍藝術(shù)片起家,但這不代表他們不懂商業(yè)和市場,不會拍膾炙人口、吸引眼球的作品。
胡雪楊執(zhí)導過《半生緣》(2003版)《白領(lǐng)公寓》等熱播電視劇。《半生緣》曾拿到上海年度收視第一,“當時同校的老師碰到我就問,后來曼楨和世鈞在一起了沒?”更讓他哭笑不得的是有次在法國為作品做后期,一位年輕人聽說他拍過《半生緣》,立刻大叫:“我小時候想看動畫片,但電視機被媽媽、外婆天天霸占著看《半生緣》,你不知道我那時候有多恨你!”
“第六代導演的風格就是沒有風格,這一代導演的基本功都很強,不是只會拍某一類型的電影。”胡雪楊自信地說,自己什么都能拍,沒有固定的電影風格。
2011年,他執(zhí)導了講述上世紀50年代和平解放阿里感人故事的《先遣連》,這是西藏自治區(qū)第一部自己制作的電影,今年,這部影片還在央視播出。2013年,胡雪楊去了法國巴黎,拍攝了兩部法語電影,一部是展示巴黎人文生態(tài)的《交錯》,另一部是以一戰(zhàn)華工為題材的紀錄片《永恒》。

這些年的豐厚積累和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也將凝結(jié)于未來的《刀俎魚肉》。“它是上海題材、上海班底的大制作,預計明年4月開拍,爭取在明年賀歲檔上映。”胡雪楊希望,在明年的這一時間,全國觀眾會討論這部電影,共同思考國家和民族命運。當然,好看的電影才能發(fā)人深省,就像他的一位朋友回憶從前看上影廠的老片子,散場后,腦子還熱烘烘的,恍恍惚惚地從新華電影院走出來,走到石門一路才冷靜下來。這是好電影帶給觀眾的特殊感受。
推薦閱讀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今日頭條

川公網(wǎng)安備5101900200431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