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孤獨(dú)裝得下天空的藍(lán),
那是一種很盛大的、
能夠容納很多東西的孤獨(dú)。
作者:劉舒揚(yáng) 侯欣穎
編輯:陳佳莉
“我怕我的靈魂死掉了,一直在‘喂飯’給它吃,所以我不停地讀書、畫畫。”
說出這話的時(shí)候,王柳云正坐在一把灰色椅子上。左手邊的粉色小電鍋里是她今天的午飯:面條、蕓豆與一個(gè)淀粉丸子的“亂燉”,清湯寡水,不見油星。
“中午畫了一陣子畫,吃得有點(diǎn)晚了。”她一邊迅速扒拉幾口,一邊向《環(huán)球人物》記者解釋。左胸前掛著的保潔員工牌,提醒著她裝載那副靈魂的身份。
去年6月,王柳云來到這棟寫字樓,日常負(fù)責(zé)15層和17層的保潔工作,包括工作區(qū)和洗手間,早上7:00開工,下午4:30參加例會,晚上7:00下班。
從保潔工作抽離,在屬于自己的世界,她還有個(gè)身份——“陋室畫家”。
在15層女廁旁的儲物間里,記者看到了她的部分畫作。一幅《釣魚島的春天》置于畫架正中央,碧波蕩漾,砂石粗糲,中間綴有幾抹綠。

·王柳云在畫《釣魚島的春天》。侯欣穎/攝
墻邊擠擠挨挨的幾幅,畫的是田野、鄉(xiāng)村,還有貓、鴨等小動物,開闊、鮮活。
一抬頭,幾件衣裙在這間不足3平方米的空間里輕輕搖擺——這就是她在北京暫住的“家”,以及大部分家當(dāng)。

·狹小空間里掛著的衣物。劉舒揚(yáng)/攝
王柳云有湖南口音,語速很快,談及心中不平事時(shí),會模仿當(dāng)事人的動作和神態(tài)。
她的身上有一種野勁,也透露出一種對抗性。這是從與這個(gè)世界長久的相處中生長出來的。她曾在的畫室負(fù)責(zé)人告訴記者,王柳云有追求,很堅(jiān)韌,也非常掙扎。
她1966年生于湖南婁底,16歲輟學(xué),被第一任丈夫家暴、卷走所有積蓄,又被現(xiàn)任丈夫呵斥“你這輩子就是給我還債的” !
幾十年間,她做過賓館服務(wù)員、工廠縫紉工、大樓保潔員,“活一天算一天”。
50歲接觸到繪畫時(shí),她突然活明白了一般,畫畫的時(shí)候發(fā)現(xiàn)“這樣可以讓自己比較快樂一點(diǎn)地活下去”。
為了學(xué)畫,也為了生計(jì),她從現(xiàn)任丈夫的老家浙江臺州,跑去福建、廣東、河南,最后來到北京,為自己編織另一個(gè)世界。
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的“大學(xué)”
我是2020年4月到北京來的,之前在河南商丘的一個(gè)鄉(xiāng)村學(xué)校教孩子畫畫,工資太低,活不下去,但也不想回家。
那時(shí)認(rèn)識了一個(gè)畫友,她在崇文門租了一個(gè)四合院,做二房東。我想,我連故宮都沒去過,有生之年要去北京看看的,在那打掃個(gè)衛(wèi)生、飯店里洗個(gè)碗,肯定能養(yǎng)活自己。做幾年攢一點(diǎn)錢,老了就可以安安心心畫畫。
剛冒出這個(gè)念頭,疫情就來了。學(xué)校不開學(xué),企業(yè)也不開門,想打工也打不成。像人家夫妻齊心協(xié)力的,能撐個(gè)一年半年,但我連半個(gè)月都不行,家里沒有半口存糧。
我趕緊問那個(gè)女孩:“我想去北京,找到工作前在你那借住幾天,可以嗎?”人家以為我是開玩笑的,讓我再等等。后來疫情越來越嚴(yán)重,我實(shí)在找不到事做,又跟她說,我真的要去北京了。她說,那來吧。我立馬買票了。
畢竟只是一面之緣,等我真到了北京,把她嚇壞了,給她發(fā)消息、打電話,兩個(gè)小時(shí)沒理我。但最后她還是把我接過去了。
隔離一結(jié)束,我到處找工作,去街上問“這里招人嗎”,看見穿這類衣服的(指了指自己)就跟上去:你是去做什么的,能不能帶上我?
像討飯一樣,我總算找到一份活,在三元橋附近做保潔。
至今我都非常感恩那個(gè)女孩,借她一步,踏過來了。

·儲物間里堆著王柳云的幾幅畫作。侯欣穎/攝
在三元橋那里做得很不容易。一起工作的有幾個(gè)五六十歲的男人,對我動手動腳。我一直想辦法離開,也根本沒心思畫畫。
我對自己說,干脆死了這條心吧。但是幾年前在福建雙溪認(rèn)識的一位老師非常關(guān)心我,希望我畫下去。
我活這一輩子,沒有愛情,沒有婚姻,沒有錢,沒有房子,沒有親情,普通人有的東西我都沒有,所以,我想自己肯定不算是一個(gè)人,就這樣活一天算一天吧。
但是這位老師,他把我當(dāng)一個(gè)“人”來看,覺得我有天賦,一直鼓勵我。
那時(shí),同住的院子里有一對善良的河南夫婦,勸我不要在那個(gè)地方受氣,錢哪里都能賺。他們有個(gè)保潔微信群,說這里(指現(xiàn)在工作的寫字樓)招工,我就過來面試,也再次拿起了畫筆。

·工作中的王柳云。侯欣穎/攝
從去年6月到現(xiàn)在,我上班幾乎什么話都不說,和所有人保持距離,存在感越低越好。
為什么要這樣?
今年2月有媒體來拍我,一個(gè)同事知道后說:“我怎么沒有那個(gè)運(yùn)氣?她長得也沒有我好看,寫的字也比不上我,唱歌也沒有我好聽,我什么時(shí)候能碰到一個(gè)人幫我拍?”
那時(shí)的領(lǐng)導(dǎo)也對我不滿:“你是在這里畫畫,還是在這里打工?你自己搞清楚!”
所以,我跟別人說什么呢?說天上的云彩、玫瑰的顏色?沒這個(gè)必要。
我天天自己一個(gè)人。我的孤獨(dú)裝得下天空的藍(lán),那是一種很盛大的、能夠容納很多東西的孤獨(dú)。

·從公司頂樓的陽臺望出去,可以看到蔚藍(lán)天空下的北京城。侯欣穎/攝
現(xiàn)在的領(lǐng)導(dǎo)對我很好,特地騰出一個(gè)空間讓我畫畫。
我喜歡在自然里自由地行走,但我既沒有錢,也沒有時(shí)間。畫每一處風(fēng)景的時(shí)候,我的心就代替了我的腳步和思維,到達(dá)了那里。雖然過會我又在掃樓梯了,但是在這一刻,我抵達(dá)了那一片天空、田地和季節(jié)。

·公司頂樓空曠的走廊,是王柳云的臨時(shí)畫室。侯欣穎/攝
我二十多歲時(shí)看高爾基的《我的大學(xué)》,里面說阿廖沙在喀山的貧民窟和碼頭完成了他的社會大學(xué)。
我想,我的“大學(xué)”應(yīng)該是在畫室里完成的。

·散落在地上的油畫顏料,是女兒兩年前給王柳云買的。侯欣穎/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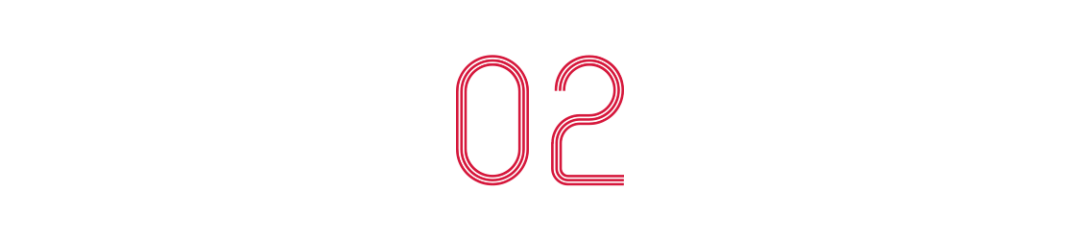
童年
我小時(shí)候體弱多病,沒人跟我玩。我就趴在草叢里,每一片草葉、每一塊石頭、每一滴露水,我都仔細(xì)觀察。我把一株草的種子剝開,看里面的小蟲子爬。我進(jìn)山里,看著眼前的石頭,想它是不是會給我開一扇門,里面會不會住著神仙?
我的母親脾氣暴躁,我的父親天生殘疾,通身的筋扭縮,如機(jī)器人。我考上重點(diǎn)高中,讀了半年,母親告訴我,家里實(shí)在沒錢了。
為了讓我的靈魂活著,我一直讀書,不停地讀。
少年時(shí)期我讀蘇聯(lián)小說。那種濃云密布的天氣里,伏爾加河流淌的深暗色水,還有土地上的那種寒冷、貧窮,以及人們的悲哀,這些我都記得。
這很符合我的心境,因?yàn)槲乙恢鄙钤诶锩妗?/p>
2017年我在福建畫畫,是用我想象中俄羅斯云彩的底色來打底的。有人很喜歡,說畫得真實(shí)。
其實(shí)這些東西都在我讀的書里,在我的心里,它們在我的靈魂深處生存了那么久,只是一個(gè)偶然的機(jī)會,我把它拿出來了而已。
30歲以后,我開始讀唐詩宋詞。開始的時(shí)候,一個(gè)字都不懂,我就一個(gè)字一個(gè)字地?fù)福哦艘稽c(diǎn)。
在農(nóng)村的生活,除了打工就是養(yǎng)小孩;跟物業(yè)公司的同事,沒有半句共同語言;同一個(gè)屋檐底下的兩人,無非就是搭伙生活……
這是一種非常孤獨(dú)的日子,我必須自己尋找意義,讀書、讀書。
通過讀書,我對自己的遭遇有一些釋懷了。在盛唐那么開放的社會環(huán)境,能夠出人頭地、富貴顯達(dá)的也屈指可數(shù),還有那么多寒門學(xué)子求師無門。

·王柳云和她的作品《山間小溪》。侯欣穎/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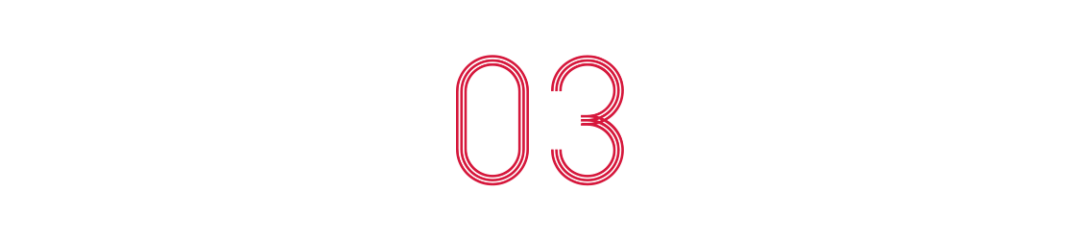
在人間
2002年開始,我在浙江的一個(gè)廠里踩縫紉機(jī),做帽子、手套、夏衣,踩了12年,把腿踩出了毛病。

·35歲時(shí)的王柳云。受訪者供圖
沒錢治病,我在床上彎彎扭扭地躺了個(gè)把月,好像躺在地獄里一樣。最后終于爬起來,我知道這份工作不能再做了。
之后,在縣里賓館做清潔工時(shí),我看到電視上說福建雙溪有一間免費(fèi)學(xué)畫的畫室。我去了,學(xué)著畫田園山水,畫小動物,還“天降奇跡”——賣畫賣了4萬塊錢。
全國各地的朋友加我微信,說你幫我畫一幅這個(gè)、畫一幅那個(gè),我好像心里有股勁一樣。我這一輩子,總是被貶損,好像不是個(gè)東西。所以,我感謝那么多人喜歡我。
帶著這些錢回到浙江,我付了蓋房的首付,買了輛汽車。蓋房一共花了十幾萬,裝修花了三四十萬,我大半輩子的錢都在里面了。
你問我老公?人家享福,他說我上輩子欠他的,那就還唄。命就是這樣。
左鄰右舍見到我,問:柳云啊,你現(xiàn)在怎么不去畫畫呀?還賣得掉嗎?
受不了這樣的“風(fēng)言風(fēng)語”,在家待了3個(gè)月,我就去了仰慕已久的深圳油畫村。那年我52歲。
我興沖沖跑到深圳拜師,人家理都不理我,把我當(dāng)一個(gè)笑話,叫我“死老太婆”。
偶然遇到一個(gè)房東,他的房子里有很大一面墻,我可以每天在那畫十幾個(gè)小時(shí),感覺很幸福。
在深圳,是女兒出的學(xué)費(fèi)和生活費(fèi),我不能讓她承擔(dān)所有壓力,就在那里找了一些事做,賺了一點(diǎn)錢,還給我老公還了兩萬塊錢的債——他沒錢就借,等我回去還。

·今年7月,記者跟隨王柳云去潘家園舊貨市場。她帶著自己的一幅作品《激浪》,說要去“碰碰運(yùn)氣”。侯欣穎/攝
2019年,一個(gè)畫友介紹我去河南教美術(shù)。沒想到的是,在河南,我對一切都釋懷了。
原來我始終對輟學(xué)這事不甘心,覺得自己怎么這樣沒有福報(bào)。但在河南的時(shí)候,我居然把《清明上河圖》臨摹出來了。之前我從沒畫過人物,臨摹《清明上河圖》,我一個(gè)一個(gè)數(shù),一共畫了361個(gè)人。這讓我非常有成就感。
我突然覺得,如果沒有那些經(jīng)歷,我也不會有現(xiàn)在,不會收獲這些珍貴奇妙的體驗(yàn)。畫畫就像放電影,它從哪里走進(jìn)去的,就從哪里走出來,然后又會走進(jìn)去。
我的經(jīng)歷和我的畫,它們是一體的。
將來,我想去西藏走走,不是現(xiàn)在,但在“上天入地”之前肯定要去的。
總監(jiān)制: 呂 鴻
監(jiān) 制: 張建魁
主 編: 許陳靜
編 審: 凌 云
(文章未經(jīng)授權(quán)不得轉(zhuǎn)載,轉(zhuǎn)載請加微信“HQRW2H”了解細(xì)則。歡迎大家提供新聞線索,可發(fā)至郵箱tougao@hqrw.com.cn。)
推薦閱讀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今日頭條

川公網(wǎng)安備5101900200431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