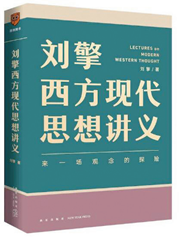2021年1月18日,學者劉擎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劉擎,1963年生于青海西寧,1978年就讀東華大學化學工程專業,1991年赴美留學,現任教于華東師范大學政治系。代表作《紛爭的年代》《懸而未決的時刻》等,自2003年起每年撰寫《西方思想年度述評》,是許多學者每年的必讀文章。2020年12月,在綜藝節目《奇葩說》第七季中擔任導師。
知乎上問:如何看待《奇葩說》第七季請劉擎當導師?
最高贊答:這么說吧,我完全是被劉擎教授的衣品圈粉的。
劉擎第一次亮相,圈領衫外搭牛仔服,背后涂鴉,袖子挽起。更多的時候,他穿的是高領衫,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的標配。
劉擎手撐在化妝臺前,看著鏡子里的自己。以往這個時候,他應該正全力以赴地寫那篇一年一度的西方思想界述評。如今,從上海華師大麗娃河畔飛到北京南五環錄影棚中,“生活一下被打亂了”,他有點矛盾,“還是喜歡回到一個不那么緊張的安靜狀態。”
當一個哲學教授出現在一檔娛樂綜藝中,事情本來就有些矛盾。在“得到”開設的課程《西方現代思想40講》中,劉擎講到了馬爾庫塞。這位在上世紀60年代風靡西方世界的思想家,提出了大眾文化與工業社會是如何塑造了“商品拜物教”和“單向度的人”。劉擎搞文化批評,諳熟這一套理論。“大眾文化對受眾的迎合、娛樂產業背后的資本運作,面對這些問題,學院知識分子總有自己的警惕和批評。”他說,“我也是這個傳統中成長的。”
“但另一方面,如果這樣一檔影響廣泛的節目,知識分子完全不參與,我們的公共領域會不會越來越狹窄?學者都在象牙塔里寫論文,但這些學術論文的平均閱讀量,大概不超過10個人。需要有人來做一個橋梁的工作,我也許不是最適合的,但愿意來試一下。”
猶豫一番,劉擎決定來《奇葩說》。他讓主持人馬東做好準備,也許節目“會被徹底搞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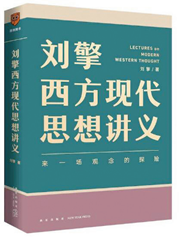
 劉擎作品:《西方現代思想講義》《紛爭的年代》。
劉擎作品:《西方現代思想講義》《紛爭的年代》。
學術的,娛樂的
馬東安慰他:不會的。
劉擎是馬東邀請來的。他在“得到”上聽劉擎講到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深以為然。哈貝馬斯認為,很多時候我們和別人達成共識,并不是某個人的道理振振有詞,說得大家啞口無言,而是因為在好好說話的氛圍下,出于彼此信任和平等尊重,大家一起把道理講通了,通過合作,建立起一個良好的公共生活。
馬東覺得,這不就是《奇葩說》在一場場針鋒相對、你死我活辯論過后的目的嗎?他需要這樣一個人,把知識性、理論性的話語引入一個娛樂節目。
劉擎于是坐在了導師席上。第一天錄制節目,他沒太緊張,還告訴馬東,10歲那年第一次上臺表演說相聲,說的就是馬季、唐杰忠二位先生的《友誼頌》,講中國支援坦贊鐵路建設。再加上年輕時打過辯論、做過演講、演過話劇,舞臺經驗還算豐富,不怎么怯場。讓他擔心的,是如何把一個學術觀點用通俗易懂又準確有力的語言表達出來,“不能晦澀,也不能簡單化”。
劉擎在努力追求這樣的平衡。他的第一個“大型圈粉現場”發生在與薛兆豐教授的辯論中。辯題是:經濟學家和哲學家,誰更容易找對象?劉擎開始想互相恭維一下對方的學科就算了,“沒想到薛老師經驗豐富,‘暗藏殺機’”。
薛兆豐先立論:學哲學的人,一看上去很博學,二容易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開脫,三可以一事無成而于心無愧,綜上,他們更容易招人憐愛、同情、原諒,更容易找對象。
劉擎開始有點不知所措,想起以前參加辯論賽的種種,“一下被年輕的自己‘附體’,腦洞激發了”。他先破了薛兆豐的立論,說對方論證的是學哲學更容易當騙子,借此發泄對人文學科的長期積怨;接著分析經濟學家如何用數據分析“收割”對象,卻不容易保持對象,最后迂回反擊:“為什么薛教授的家庭這么幸福美滿呢?因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身上有深藏已久的哲學家的品質。”
劉擎把它看成一場“好玩的表演賽”。“我想表達的是,哲學并非與現實無關,只是不痛不癢地講一些好聽的修辭。當我們表達一個觀點時,它背后的前提和假設未必就是理所當然的,哲學是來幫助我們揭示、反省這些不言自明的前提和假設,讓我們成為一個更自覺、更明白的人。”
他希望完成這個揭示的工作。節目第八期有一個辯題:下班后的工作消息該不該回?有人說“回”,這是職場不言自明的規則,是每個“打工人”必須付出的代價。劉擎則堅持“不回”,在逐漸激昂的BGM里,音量不斷提高:“這個世界應該讓那些不好的選擇消失。因為人不只是有效率,不只是被當作成本收益計算的符碼,人是作為目的的存在,不僅僅是發展的工具。忘記這一條,我們就會變成現實的奴隸。”
節目彈幕中,不時飄過那句年輕人耳熟能詳的歌詞,“生活不只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劉擎倒覺得,詩不只在遠方,眼前也不只有茍且。“因為‘茍且’時心中尚存的不安,就是你眼前的第一行詩。”
左圖:1985年,“文青”時期的劉擎。右圖:2019年1月,劉擎與同行友人聚會。
好玩的,深刻的
劉擎曾是個詩人,最知名的作品是《四月的紀念》,寫于1985年,后來被喬榛、丁建華朗誦,成為配樂詩朗誦中的經典。
他的文學啟蒙,是8歲時讀到的長篇小說《高玉寶》。上世紀50年代,父母響應國家號召,從上海奔赴青海,一留20年。隔壁小伙伴的母親,是師范學院圖書館的管理員。1974年暑假,劉擎他們偷了鑰匙,去了“文革”后被封閉的書庫,開門的一瞬間,幾萬本書躺在灰塵中,昏暗的光線照在一張張蜘蛛網上。
印象最深的書,是一本繁體字版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多年以后,劉擎在一首題為《1974年的閱讀與情感》的詩中回憶,11歲的自己,處在“彷徨而無從墮落的歲月,一個布爾喬亞的少女成為你僅有的心事,從此,革命一直使你無限憂傷”。
1978年,劉擎考入華東紡織工學院(現東華大學)化學工程系,學高分子化學。思想解放之風彌漫校園,大學生們三五一堆,討論各種大問題就是最大的娛樂消遣,“好玩的和深刻的,我們不太分”。那一年,劉擎15歲,宿舍流行臥談會,大齡同學們分享在工廠、農村的插隊故事,構成了他青春期的社會歷史教育。
那時的劉擎,以演講才能而聞名,擅長運用知識界時髦的概念。每逢周六晚上,他就要到上海青年宮演講,有人回憶那時的他,一成不變的五五開發型,一本卷起來的16開雜志握在手中,權當道具。
當時,“文化熱”興起,尼采、弗洛伊德和薩特是熱門人物,劉擎把能找到的中譯本都收齊了,熬夜讀書。“現在回頭看,薩特可能不是第一流的哲學家,弗洛伊德的很多理論有問題,尼采當然是個曠世奇才,但對他的闡釋是多種多樣的。”
“文化熱”中出現了三個活躍的知識群體:以湯一介、李澤厚為主力的中國文化書院,通過開班授課啟蒙大眾,導師有梁漱溟、馮友蘭、季羨林、金克木等一眾名家;以甘陽、趙越勝為主力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出版了“現代西方學術書庫”“新知文庫”等上百種讀物,其中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尼采的《悲劇的誕生》影響一代學人;而以金觀濤、劉青峰為靈魂人物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匯聚了王岐山、張五常、茅于軾、董秀玉、李銀河等,影響遍及官方民間,從1983年到1988年,以平均每年一批的頻率,總共出了5批74種書。
這些書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完全是新知識、新觀念、新思想。研二那年,劉擎在一次講座中,看到有位老師把“走向未來”叢書里的幾本拿出來,一下被吸引,從此開始收集,一本不差地買全了。
1988年10月,成都一次學術討論會上,25歲的劉擎認識了41歲的金觀濤。那時,他只是上海一家雜志的特約記者,金觀濤則早已“名震廟堂”。飯桌上,他們就卡爾·波普爾的一個問題爭論起來,晚上,金觀濤來到劉擎的房間,兩個理工科出身的人搭上了交流的天線,“似乎很‘邏輯地’,他收我做了‘學徒’”。
在金觀濤的引介下,劉擎走進了王元化的客廳,那里永遠高朋滿座,三教九流各種聲音,無所不有。他結識了許紀霖、蕭功秦、高瑞全、朱學勤等人,一只腳踏進了學術思想圈。
另一個朋友圈,來自文藝界。那時,出了一個新劇本、《收獲》上發表了一批新小說,劉擎就會找孫甘露等作家朋友一起閱讀討論。他和陶駿、張昭、劉洋四人成立了“白蝙蝠”劇社,排演過一個四幕詩劇《生存還是毀滅》。張昭演哈姆雷特,陶駿演麥克白,劉擎請來林棟甫演李爾王,自己演現代人,服裝是麻袋片做的,走“貧困戲劇”風格,10平方米就能演出。
1990年,劉擎赴美留學。走之前,他請朋友們吃飯,把自己的詩集分送給大家,是用鋼板蠟紙刻了油印的,薄薄的一冊。他的文青歲月,就此落幕。
匯聚的,分離的
1991年8月,劉擎到馬凱特大學讀政治學碩士。“nice(很好)的地方,nice的學校,nice的人。”多年后,他在知乎如此形容那段讀書生活,3年后,又去了明尼蘇達大學讀博士。
知識界已改天換地,80年代思想與學術混沌一片、生氣淋漓的景象不再。“80年代的學術,現在看來并不那么成熟精道,甚至有些粗糙,但它有原生的生命活力,思考真正的大問題。現在,我們的學術做得太規范了,學科本身形成了‘內卷’的發展,我們為什么寫文章?是為了發表在權威刊物,還是它關乎我們的時代和每個人的生活?我們要重返這些問題,這是人文科學的初衷,不要忘了自己的來時路。”劉擎說。
2003年,劉擎落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從那一年開始,他每年年末都要撰寫一篇西方思想界的年度述評。學者陳嘉映說:“特別值得讀,國內沒有第二個人能夠寫出來。”
去年,陳嘉映的新書《走出唯一真理觀》出版,劉擎和他有一場對談。“唯一真理觀的麻煩是,它讓我們確信通過理性探索可以掌握規律,把握自己和時代的發展。在這樣一種信念中,我們會喪失謙遜,喪失對自我的批判和懷疑。”劉擎說,“我們需要哲學,因為我們并不能假定誰可以真理在握,因此需要永恒的探索和永恒的對話。”
如果單挑一位哲學家,和他上《奇葩說》打一場辯論,劉擎會選德國哲學家卡爾·施密特。“他認為政治就是敵我分明,但更深刻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和自己不同甚至敵對的人共處。這不是小到個人、大到世界的更根本的問題嗎?”
 《奇葩說》中,劉擎(右)與薛兆豐就“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誰更容易找對象”,展開辯論。
《奇葩說》中,劉擎(右)與薛兆豐就“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誰更容易找對象”,展開辯論。
2020年新年,劉擎開始寫《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評》。英國脫歐、美國退守、WTO失靈、貿易爭端加劇、民族主義勃興、排外浪潮洶涌……他如此描述當下的世界:“分裂與離散開始主導時代潮流,人們講述著各自不同的‘小故事’,而‘大寫的歷史’似乎已消失隱匿。”
但他始終相信,人類的歷史是一個“經由沖突、達至共通、終于匯聚”的故事——我們分享著共同的命運,匯聚不必因為彼此喜歡,而是因為面臨共同的威脅和挑戰。就像羅貫中在《三國演義》里所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或者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更明確的信念:“合久必分只是一時,分久必合才是不變的大趨勢。”
近4萬字的述評,劉擎寫了一個多月。接著,疫情開始了。新冠肆虐的2月,他在“得到”開課,講解20世紀西方現代思想,從“現代思想的成年里程碑”馬克思·韋伯到“后冷戰時期”的亨廷頓與福山。
4月1日,《西方現代思想40講》最后一課更新。劉擎告訴大家的最后一句話是:“人類因為理性而偉大,也因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
那一天,經歷漫長宅家生活的劉擎,出門參加了朋友的聚會,海闊天空,聊到很晚。編輯發來微信,告知訂閱用戶過了2萬。這個數字在“得到”APP上不算什么,但他還是開心。席間,大家熱烈討論,為各種極端化的觀點和言說方式憂心忡忡。劉擎想,聽過他這門課的朋友,以后和人說話,甚至爭論,大概會不一樣吧?
“兩萬多人,就是兩萬多粒沙子。也可能,會是兩萬多粒種子吧。”回家路上,劉擎這樣想著,感覺有些欣慰。久違的夜色中,燈火斑斕。(本刊記者 許曉迪)